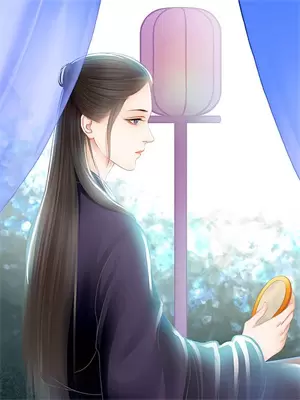这是一段几乎真实的经历,我真的见了她,在那个最青春澎湃的年纪。1999年,
农历七月半这天夜里,长久被厂区深夜传来异响声折磨的我,实在愤怒了。
前的许多这样的日子里,我给冥冥中可能存在的东西,写过乞和书,伴着黄纸和白纸,
烧过给它们,还泼过水饭,又烧过香烛元宝。可是,一点毛用没有。尤其七月半这几天夜里,
它们更是在午夜,列队一样,穿梭在寂静的一层楼的宿舍外面。那声音,穿门而过,
清晰的如蚯蚓一样,爬进我的耳朵。于是,七月半半夜,正当门外又响起一连串脚步声时,
我颤抖着双手,从墙上拔下另一个老同志从道观请来的柳木长剑,双腿打抖的打开了门。
闭着眼一阵疯劈乱砍之后,我又大叫着,绕着这些房子在空气中砍了一圈。随后,
我顺着前院,绕到了这占地二三十亩的,处在大山脚下的宿舍广场的后面。这里,
栽着占地几十亩左右的沙棘树,围墙外面三百多米,
是一片不知存留了多少个百年的一片乱葬岗地。横七坚八的死人,躺在哪里。
遇了夏季的雨夜,你能真切的听到呜咽的声音,像有人在耳边哭,忽远,忽近。
既然都烧了乞和书给它们,它们还这么要吓我,就拼了吧!砍了一圈回来,我又在门口,
窗台上泼上了我中午准备好的黑狗血,指望着这些东西,能挡住藏在黑暗里的东西。
现代量子试验证明,当我们以观察者的视角审视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切才塌缩为一种可能,
可是,在我们目光之外呢?是不是一切都存在,一切都有可能?我们看不到很多的光波,
听不到很多的声波,更加无法看到电子,那么我们可是否可以以为?这些东西不存在?
你看得到风吗?还有空气?躺在被子里的我,盯着垂下来的窗帘布。耳边,
响起了奶奶的话。孩子,我们这个世界,连通着许多其它的世界。有的,我们看得见,
有的,我们看不见。但你要相信,就算是在看不见的世界里,也有善恶之分的。这夜的雨,
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弄完这一切的我缩在被子里,
牙齿打颤的声音在寂静的宿舍里格外清晰。窗外的沙棘树被风刮得簌簌响,
混着远处乱葬岗隐约的呜咽,像无数根细针,扎得人心里发紧。就在这时,
一阵极轻的叹息声飘了进来,不是来自窗外,而是就在我的床边。汗毛和头皮瞬间竖了起来。
我猛地屏住呼吸,张大眼睛四处找寻。灯光如炽,随着窗外透进来的一点月光,
我看见一个模糊的影子蹲在地上,身形纤细,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你,
你是什么东西?我声音打颤,强作镇定的问。她没有立刻靠近,
只是用透明得几乎要消失的手指,轻轻拢着地上溅落的黑狗血,
动作轻柔得像是在收拾打碎的琉璃。那黑狗血本是我用来驱邪的,此刻在她指尖下,
竟像是有了生命,顺着她的指缝缓缓聚拢,又慢慢渗进水泥地的缝隙里,没留下一点痕迹。
你别怕。之前你写的乞和信,我看过了,但我不能经常出来,只有像今天这样的机会,
我才可以显形,让你看见我!她的声音细弱如丝,带着点怯生生的沙哑,
像是很久没有说过话。我浑身僵硬,想叫,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发不出一点声音。
她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恐惧,慢慢抬起头,月光落在她脸上,我这才看清,
她的脸不是我想象中血肉模糊的模样,而是透着一种月光般的苍白,眉眼清秀,鼻梁小巧,
只是眼底藏着化不开的愁绪,像蒙着一层永远散不去的雾。她的头发不湿漉漉地粘在脸上,
而是柔顺地披在肩头,发梢偶尔会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晃动,带着点虚幻的质感。
我不是来害你的。她往旁边挪了挪,尽量离我的床远了些,姿态里带着明显的讨好,
我只是……太孤单了。她飘到窗边,指尖轻轻划过玻璃上的霜花,留下一道淡淡的白痕,
很快又消失不见。这里的夜里太静了,静得能听见自己骨头腐烂的声音。
我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哪怕只是听听你的呼吸声也好。孤单?你也会孤单么?
我一个班就是三个月,与身边的工友形同陌路,他们以为我是靠关系,
走后门进的这个变电工场。乱葬岗里的那些先人,早已步入了轮回或是消散不见的,
现在就剩了我一个她并未接话,似乎自言自语。我盯着她透明的手腕,
那里隐约能看到一道深紫色的勒痕,像一条狰狞的蛇,盘踞在她纤细的皮肤上。
她似乎注意到了我的目光,慌忙将手藏到身后,脸上露出一丝局促的红晕,
虽然那红晕在她苍白的脸上显得格外诡异,却奇异地冲淡了几分恐怖。对不起,
是不是吓到你了?她轻声说,身体微微往后退了退,几乎要贴到冰冷的墙壁上,
我马上就走,以后再也不打扰你了。或许是她如此寂然和贴心的理解,我心颤了一下。
沙哑地喊了一声:等等!她停下脚步,疑惑地回头看我,眼底的愁绪里多了一丝惊讶。
我咽了口唾沫,鼓起勇气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她愣了一下,
嘴角慢慢勾起一个极淡的笑容,那笑容像初春的冰雪初融,带着点脆弱的温暖。我叫林珍。
她说,以前,我也在这个厂区上班。你来这里三年了,我熟悉你的一切。
那天夜里,林珍没有走。我也并不敢,再与她多说什么。沉默的时光里,
她就飘在房间的角落里,安安静静地陪着我。我睡不着,
她就轻声给我讲厂区以前的事——讲春天时沙棘林里会开细碎的小白花,
讲夏天的夜晚工友们会在广场上乘凉,讲秋天的落叶会铺满宿舍前的小路。她的声音很轻,
像羽毛一样拂过我的耳畔,那些原本阴森的夜晚,竟渐渐变得安稳起来。我后来才知道,
那些夜里列队穿梭的脚步声,其实是她一个人在宿舍外徘徊,她只是想靠近一点,
听听活人的声音,驱散自己无边无际的孤独。从那以后,厂区的深夜不再是恐惧的代名词。
我写东西到深夜,桌上会凭空多出一杯温凉的水,水温总是刚刚好,不烫也不凉,
像是有人特意晾过。有一次供电设备出问题,我加班到凌晨三点,趴在桌上睡着了,
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人轻轻为我披上了一件外套——那是我白天晾在阳台上的工作服,
不知何时轻柔的盖在了我的身上。我睁开眼,看见林珍正站在桌旁,
小心翼翼地帮我把外套的领口拢好,动作轻柔得生怕惊醒我。夜里凉。她轻声说,
眼底满是关切。起夜时,走廊里的声控灯总会提前亮起,橘黄色的光顺着走廊蔓延开来,
映着林珍站在尽头的身影。她不会靠近,只是远远地站着,像个安静的守护者,
等我上完厕所回到房间,她才会慢慢飘过来,继续陪在我身边。有一次,
走廊里的声控灯坏了,我摸着黑往前走,心里难免有些发怵。就在这时,
我看见前方不远处亮起了一点微弱的蓝光,是林珍的指尖散发出来的。那蓝光很淡,
却足够照亮我脚下的路,她一路在前边引路,直到我安全回到房间,蓝光才渐渐消失。
林珍很喜欢厂区后面的沙棘林。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她就会飘到沙棘林里,
静静地站在一棵最粗的沙棘树下。我问她为什么总待在这里,
她指着那棵树的根部告诉我:我生前最喜欢在这里种野花,每年春天,
这里都会开一片黄色的小菊花,特别好看。说这话时,她的指尖会泛起淡淡的粉色,
像沾染了春日的阳光,眼底的愁绪也会淡去几分。有一次,
我特意从山下的集市上买了一包野菊花的种子,撒在了那棵沙棘树下。
林珍看着我挖坑、播种,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笑容,那笑容像阳光一样,
驱散了她身上的阴寒气,让我几乎忘记了她是一个鬼。谢谢你。她轻声说,
声音里带着哽咽,我以为,再也不会有人记得我喜欢什么了。她飘到我身边,
透明的手轻轻拂过那些刚种下的种子,像是在抚摸自己的孩子。等明年春天,
它们开花的时候,我一定叫你来看。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林珍之间的默契越来越深。
我会把白天听到的厂区八卦讲给她听,她会静静地听着,
偶尔发表几句自己的看法;她会告诉我厂区里哪些地方藏着秘密,
比如仓库后面的废弃防空洞,比如办公楼三楼最西边的房间,那里曾是她上班的地方。那天,
我因为工作失误被领导批评,心情格外低落,回到宿舍就趴在桌上哭了起来。
林珍默默地飘到我身边,没有说话,只是用她透明的手轻轻拍着我的后背,
那动作带着一种笨拙的温柔,却奇异地安抚了我烦躁的心。别难过。她轻声说,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她飘到窗边,指着远处的大山说:你看,山那么高,路那么远,
你都能走到这里,这点小事,算不了什么的。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坚定的力量,
让我慢慢平静了下来。我开始好奇林珍的过去,想知道她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每次我提起这个话题,她都会眼神躲闪,不愿意多说。直到有一天,
我在厂区的旧档案柜里翻找资料时,偶然发现了一份二十年前的事故报告。
报告上写着:1998 年 7 月 15 日,我厂女工林珍在宿舍区失踪,
经多方搜寻无果,推测为意外走失。报告的附件里,有一张林珍的照片,
照片上的她穿着蓝布工装,笑容灿烂,眼神清澈,和我现在看到的她一模一样,
只是少了几分阴寒,多了几分鲜活。我拿着报告回到宿舍,林珍正坐在窗边,
看着外面的沙棘林发呆。我把报告递给她,她的目光落在照片上,身体突然剧烈地颤抖起来,
透明的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从她的眼角滑落,却落不到地上,只能化作一缕缕白雾,
轻轻拂过我的脸颊,带着点微不可察的凉意。他们骗了人。她的声音带着哭腔,
我不是走失的,我是被人害死的。林珍终于向我讲述了她的遭遇。二十年前,
她在厂区的财务室上班,偶然发现了厂长和会计勾结,挪用公款的秘密。为了掩盖罪行,
厂长和会计在一个深夜将她骗到沙棘林里,残忍地杀害了她,还伪造了她走失的假象。
他们用绳子勒死了我,她指着自己手腕上的勒痕,声音颤抖,
然后把我的尸体埋在了沙棘林的最深处,还把我最喜欢的那枚银簪扔在了树洞里,
说要让我永远也不能超生。我看着她苍白的脸,心里一阵发酸。这么多年来,
她一直被困在这里,承受着孤独和痛苦,却连一个倾诉的人都没有。我帮你。
我握住她透明的手,虽然感觉不到一丝温度,却异常坚定地说,我一定帮你找到证据,
让那些凶手受到应有的惩罚。林珍看着我,眼里充满了感激,仿佛有眼泪,要涌了出来。
谢谢你,她轻声说,这么多年了,终于有人愿意相信我了。接下来的日子,
我开始四处寻找证据。林珍凭着记忆,
带我找到了她被埋尸的地方——就在沙棘林最深处的那棵粗沙棘树下。我拿着铁锹,
一点点地挖着泥土,林珍就飘在我身边,紧张地看着我。挖了大约两米多深,
铁锹突然碰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我心里一紧,加快了挖掘的速度。很快,
一具早已腐烂的骸骨出现在我的眼前,骸骨的脖子处有明显的骨折痕迹,
和林珍说的一模一样。在骸骨旁边,我找到了一个小小的树洞,里面果然藏着一枚刻着珍
字的银簪,银簪已经氧化发黑,却依然能看出当年的精致。除了骸骨和银簪,
我还在树洞里找到了半张被撕碎的欠条,上面写着厂长向林珍借钱的字样,金额巨大,
落款日期正是林珍失踪前的几天。我知道,这就是厂长杀人灭口的直接证据。
我拿着这些证据,毫不犹豫地报了警。警察很快就赶到了厂区,对现场进行了封锁和勘查。
当警察将骸骨挖出来的时候,林珍飘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眼泪不停地滑落。爹,娘,
我终于可以瞑目了。她轻声说,声音里带着释然。警察根据我提供的证据,
很快就逮捕了已经退休的厂长和会计。面对铁证,他们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当法院宣判他们一个死刑,一个无期徒刑的消息传来时,林珍高兴得像个孩子,
在宿舍里飘来飘去,透明的脸上满是灿烂的笑容。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她飞到我身边,
轻轻地抱了抱我,虽然我感觉不到她的体温,却能感受到她内心的喜悦和感激。从那以后,
林珍变得开朗了许多。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总是愁眉苦脸,而是经常会主动和我说话,
甚至会学着我平时的样子,在宿舍里看书写字——虽然她的手根本碰不到书页和笔,
却依然做得津津有味。有一次,我买了一台收音机,晚上的时候就打开听戏曲,
林珍也会凑过来,静静地听着,偶尔还会跟着哼唱几句,声音轻柔,很好听。
她还会帮我留意厂区里的异常。有一次,一个小偷潜入厂区,想偷仓库里的设备。
林珍发现后,立刻飘到我的房间,用她的方式提醒我——她轻轻吹动桌上的台灯,
让灯光忽明忽暗。我察觉到不对劲,立刻拿起手电筒,跑到仓库里,正好撞见小偷正在作案。
我大喊一声,小偷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跑,最后被厂区的保安抓住了。事后,
我对林珍说:谢谢你啊,要是没有你,仓库里的东西肯定就被偷了。
林珍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这没什么,我只是不想让你受到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