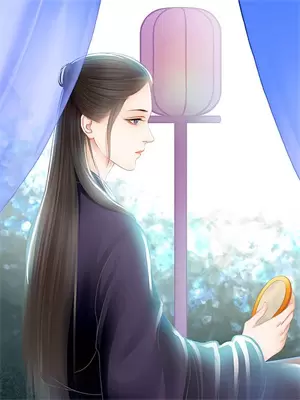十二月的纽约,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街道。但在我们的小公寓里,壁炉里的火正烧得旺。
凯正蜷缩在我怀里,手里拿着一张新罕布什尔州的地图,
指尖在一个叫汉诺威的小镇上打着圈。你看,这里有最好的法学院,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俏皮的憧憬,我们可以买一栋带白色栅栏的房子,养一条金毛犬,
生两个孩子。他们会有蓝眼睛,不会说意大利语,
也永远不知道‘Consigliere’是什么意思。我笑了,收紧了抱着她的手臂。
这正是我们一遍遍描绘的未来——一个与“科莱昂”这个姓氏无关,
干净、透明、沐浴在阳光下的未来。我胸前的战争勋章曾为这个国家带来荣耀,现在,
我只想让它成为我个人生活的通行证,通往一个没有枪声和密谋的平凡世界。
就在我准备亲吻她的时候,电话铃声响了。那声音尖锐、突兀,像一声警报,
瞬间撕裂了壁炉里最后一丝温暖的噼啪声。凯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我们都清楚,
会打到这间公寓的,只可能是那个我拼命想逃离的世界。我拿起听筒,是我大哥桑尼。
他的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每一个字都带着滚烫的血腥味,几乎要从听筒里喷出来。
迈克尔!父亲……父亲在街上中枪了!轰——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我脚下分崩离析。
凯的惊呼声、窗外的车鸣声、墙上时钟的滴答声……所有声音都像被吸入一个黑洞,
只剩下桑尼那句咆哮在我耳边无限循环,震得我耳膜生疼。父亲。
那个在我眼中如神祇般存在的男人,
那个用沉默和威严统治着整个纽约地下世界的维托·科莱昂,中枪了。我挂断电话,
手指冰冷得不听使唤。我看着凯惊恐的眼睛,却无法说出任何一句安慰的话。
我能从她清澈的瞳孔里,看到那个正直、无辜的战争英雄正在龟裂,从裂缝里,
一个我自己都感到陌生的、冰冷的灵魂,正缓缓苏醒。我一直逃避的那个世界,
终究还是找上了我。我的战争,从这一刻起,才算真正开始。当我赶到医院时,
走廊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和廉价雪茄混合的古怪味道。桑尼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
通红着双眼,正揪着家族军师——我的养兄汤姆·黑根的衣领咆哮。
看着桑尼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我知道,家族的未来如果交到他手上,
不出三天就会被他一头撞得粉碎。他们说情况很危险,汤姆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冷静,
但这冷静在桑尼的狂怒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五颗子弹,但……他还活着。还活着。
这三个字像一剂强心针,让我几乎停止跳动的心脏恢复了些许功能。我穿过人群,
透过病房门的玻璃窗,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父亲。他身上插满了管子,脸色灰败,
曾经那双能洞察一切的眼睛紧闭着。那个无所不能的“教父”,
此刻只是一个脆弱的、濒临死亡的老人。就在这时,我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太安静了。
这里是科莱昂家族族长的病房,门口本该守着我们最精锐的人手,
本该有被金钱喂饱的警察在四周巡逻。可现在,除了我们几个核心成员,这里空无一人。
一股冰冷的寒意从我的脊椎升起。这不是疏忽,这是一个陷阱。他们要进行第二次暗杀。
保镖呢?我抓住一个手下,声音低沉得发紧,警察呢?都去哪儿了?
那人一脸茫然:桑尼哥发了火,让他们都去街上找线索了……我看向桑尼,
他还在因为愤怒而失去理智。我立刻明白,不能指望他了。我转身冲出医院大门,
寒风灌进我的肺里,让我瞬间清醒。门口,一个面包师,恩佐,正焦急地徘徊。
他是父亲帮助过的人,此刻是来探望恩人的。我看着他那张写满忠诚和恐惧的脸,
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我脑中瞬间成形。你想救我父亲吗?我盯着他的眼睛。
他毫不犹豫地点头。很好,我脱下我的军大衣,披在他身上,将衣领立起,
遮住他半张脸,现在,站到我身边来,手插进口袋里,就像里面有枪一样。别说话,
别发抖,跟我一起站在这里,盯着每一辆开过来的车。恩佐的牙齿在打颤,但他照做了。
于是,在那个致命的夜晚,医院门口,一个战争英雄和一个瑟瑟发抖的面包师,
伪装成了两个冷酷的杀手,构成了科莱昂家族唯一的防线。几分钟后,
一辆黑色的轿车缓缓驶来,在医院门口停下。车灯像恶魔的眼睛,直勾勾地扫过来。
我能感觉到身边的恩佐几乎要瘫倒在地。我用胳膊肘狠狠顶了他一下,
自己则将手伸进大衣口袋,做出一个拔枪的姿势,眼神冰冷地与车里的人对视。那几秒钟,
漫长得像一个世纪。最终,那辆车没有熄火,它只是停顿了一下,然后,
缓缓地、不甘心地开走了。我知道,我们赌赢了。然而,危险并未解除。几分钟后,
一辆警车呼啸而至,车上走下来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男人——警察局长麦克劳斯基。
他那张肥胖的脸上,写满了被金钱和权力浸透的傲慢。他不是来保护我们的,
他是来为杀手清除障碍的。你们在这里干什么?滚开!他咆哮着,一股酒气扑面而来。
我们在保护我的父亲,维托·科莱昂。我站直身体,挡在他面前,而你,局长,
你的手下都去哪了?他显然没把我这个“干净”的科莱昂放在眼里,眼神里满是鄙夷。
我不管你是谁,小子,我让你滚!那些人收了索拉索的钱,你也是。我的声音不大,
却像针一样刺穿了他伪装的权威。麦克劳斯基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他被我说中了。
恼羞成怒之下,他挥起了他那粗壮的拳头。我没有躲。那一拳,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左脸上。
我甚至听到了自己下颌骨发出的、令人牙酸的碎裂声。冰冷的水泥地撞上我的脸颊,
除了浓重的血腥味,我还能尝到砂砾的粗糙感。那一刻,我想起的不是疼痛,
而是战场上子弹擦过耳边的呼啸。但我没有倒下。我扶着墙,缓缓站直,
用一种全新的、冰冷的目光看着他。那一拳,打碎的不仅仅是我的骨头,
更是我对这个国家法律与秩序的最后一丝幻想。我明白了,在这个世界里,没有所谓的正义。
所谓的秩序,只是权力者用来粉饰暴力的遮羞布。当这层布被撕开,剩下的,
只有最原始的丛林法则。你可以杀人,只要你有足够的权力让警察为你开路。
回到家族的指挥部——我父亲的书房时,那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大哥桑尼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野兽,狂躁地砸着东西,嘴里不停地咒骂着,
他只想立刻召集所有人手,和五大家族全面开战。我要杀了他们!
我要让整个纽约血流成河!汤姆·黑根拼命地想让他冷静下来,分析着开战的利弊,
但在桑尼那被怒火烧光的理智面前,任何分析都像是在对牛弹琴。其他的头目们则分为两派,
一派支持桑尼的复仇,另一派则忧心忡忡,担心家族会在这次战争中元气大傷。
这里没有领袖,只有一盘散沙。我默默地走进房间,脸上的剧痛让我无法做出任何表情。
我找了个角落坐下,听着他们的争吵,像一个局外人一样,冷静地分析着眼前的局势。
索拉索,那个胆大包天的毒枭,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他不仅想杀我的父亲,
还买通了警察局长。他们算准了桑尼的冲动,也算准了我们家族在失去领袖后的混乱。
他们不会善罢甘休。战争,不可避免。但像桑尼那样毫无策略地冲上去,只是自取灭亡。
必须有人站出来,结束这场混乱。必须有一个计划,一个能一击致命、扭转乾坤的计划。
我的目光扫过房间里的每一个人。暴躁的桑尼,谨慎的汤姆,
摇摆不定的头目们……没有一个人能承担这个角色。那么,只能是我了。
在所有人争吵到筋疲力尽,房间里出现短暂的死寂时,我缓缓地站了起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身上,带着疑惑、同情,或许还有一丝轻视。在他们眼里,
我只是那个需要被保护的、不谙世事的小儿子。我走到地图前,
我的声音因为脸上的伤而有些含糊,但每一个字都清晰无比,带着不容置疑的冷静。
索拉索会要求再次谈判。我说,他想杀父亲没成功,现在我们是平等的。
他会找个地方,一个他认为绝对安全的地方,和我们谈。他会要求我们保证他的安全。
桑尼不耐烦地打断我:谈什么谈!老子要他的命!我没有理他,
继续说道:他会带着麦克劳斯基一起去。因为那个条子现在和他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他认为,有警察局长在场,我们绝对不敢动手。汤姆皱起了眉:迈克尔,
你的意思是……是的。我转过身,迎着所有人的目光,平静地投下了一颗炸弹。
他们会搜我的身,确保我没有带武器。但没关系,
我会提前让人在谈判餐厅的厕所里藏好一把枪。我会借口上厕所,拿了枪出来,然后,
杀了他们两个。整个房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用看疯子一样的眼神看着我。
那个温文尔雅的战争英雄,那个连家族会议都很少参加的迈克尔,此刻,
正在冷静地、详细地阐述一个刺杀警察局长的疯狂计划。桑尼甚至笑出了声,
那笑声里充满了嘲弄:你?迈克尔?你以为杀人是去战场打靶吗?你连枪都没碰过几次!
你会吓得尿裤子!我没有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这不是个人恩怨,桑尼。
我的声音冰冷得没有一丝温度,这是生意。杀了索拉索,我们斩断了敌人的头。
而杀了麦克劳斯基,我们向整个纽约的黑白两道传递一个信息——科莱昂家族,不是好惹的。
他们动了我们的人,就要付出十倍的代价。这能为我们赢得时间,赢得重整旗鼓的时间。
我的话,让在场所有老于世故的头目们都陷入了沉思。他们第一次,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我。
汤姆担忧地看着我:迈克尔,杀了警察,会引来所有警察的报复,这太冒险了……
一个收黑钱、贩毒、参与谋杀的警察,不是警察。我打断他,
报纸会把他写成一个败类。我们可以收买记者,我们可以制造舆论。汤姆,这些你比我懂。
房间里再次陷入沉默。我的计划,疯狂,但又充满了致命的诱惑力。
它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指向了敌人的心脏。最终,我结束了这场讨论。
我看着大哥桑尼,看着养兄汤姆,看着所有叔伯辈的元老们,
用一种他们从未听过的、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出了那句改变我一生的话。我去杀。
我要亲手杀了索拉索,还有那个条子。我的宣言像一块石头砸进了死水里,
激起的不是赞同,而是更大的混乱和质疑。桑尼第一个跳了起来,
他那张涨红的脸因为嘲讽而扭曲,指着我的鼻子,仿佛在看一个天大的笑话。你?迈克尔?
省省吧!你连怎么用枪线上膛都不知道!战争英雄?这里不是诺曼底,这里是纽约!
对方是索拉索,是塔塔利亚家族!他们会把你像一只小鸡一样捏死!
几个叔伯辈的元老也纷纷摇头,他们的眼神里充满了怜悯和不信任。在他们眼中,
我永远是那个在常青藤校园里读书的孩子,是科莱昂家族的异类,干净得不属于这片泥潭。
只有汤姆,我们的军师,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我,他看到了我计划背后的疯狂,
也看到了那疯狂之下冰冷的逻辑。我没有理会桑尼的咆哮。
他的愤怒就像一桶泼在地上的汽油,看起来声势浩大,却只会烧光自己,什么也留不下。
我走到他面前,直视着他那双燃烧着怒火的眼睛,我的声音依旧平稳,
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穿透力。桑尼,你告诉我,开战以后呢?和五大家族火并,
我们的**、工会,所有生意都会陷入停滞。每天烧掉的钱会是个天文数字。
警察会像苍蝇一样围上来,到时候我们面对的就不仅仅是塔塔利亚了。你想过这些吗?
我的问题像一盆冰水,浇熄了他一部分气焰。他张了张嘴,却说不出一个字。
我转向那些元老们。各位叔叔,父亲教导我们,永远不要憎恨你的敌人,
那会影响你的判断力。桑尼现在被愤怒冲昏了头,而你们,难道也要跟着他一起疯狂吗?
我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个人。我的计划,不是为了泄愤,是为了生存。索拉索是蛇头,
麦克劳斯基是毒牙。只有同时斩断蛇头、拔掉毒牙,这条毒蛇才会暂时瘫痪。而我们,
需要的就是这段时间。我们需要时间来稳住阵脚,找出内鬼,然后,
再把他们一个个连根拔起。书房里死一般寂静,只剩下老式挂钟沉重的滴答声。我的话,
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剖开了他们被情绪蒙蔽的大脑,让他们看到了血淋淋的现实。最终,
是家族里最老谋深算的头目克莱门扎,那个胖得像座肉山的男人,缓缓点了点头。
他的声音沙哑而沉重:这孩子……说得有道理。桑尼,让他试试。
桑尼像一头泄了气的皮球,颓然坐回沙发里。他输了,不是输给了我的勇气,
而是输给了我的冷静。在这间象征着家族权力的书房里,我第一次,用智慧而不是拳头,
赢得了话语权。计划就这样定了下来。接下来的两天,我像一台精密的机器,
学习着杀人的每一个细节。克莱门扎亲自教我如何使用那把小巧却致命的左轮手枪,
如何感受它在掌心冰冷的重量,如何在一秒钟内完成拔枪、上膛、射击。他还反复叮嘱我,
枪会用胶带粘在老式厕所的水箱后面,开完枪,就立刻扔掉,
然后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走出来。最重要的是,迈克尔,他拍着我的肩膀,眼神复杂,
当你走出厕所的时候,脑子里不要去想那两个倒在血泊里的人。你要想你的家人,
想你为什么这么做。否则,你会崩溃的。谈判的地点定在布朗克斯的一家小意大利餐厅。
索拉索选的地方,他认为那里是他的地盘,绝对安全。去赴约的那天晚上,纽约下起了小雨,
冰冷的雨水敲打着车窗,像是在为我送行。车里,索拉索坐在我身边,
用一种猫捉老鼠的眼神打量着我,嘴里说着虚伪的客套话。麦克劳斯基则坐在副驾驶,
从后视镜里冷冷地瞥着我,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死人。我的心脏在胸腔里剧烈地跳动,
手心全是冷汗。但我知道,我不能表现出丝毫的恐惧。
我必须扮演一个惊慌失措、急于求和的软弱继承人,让他们放下最后的戒心。
我父亲……他是个老派的人,我开口,声音带着刻意伪装的颤抖,他不懂得变通。
但是我们年轻人可以合作。只要你们保证我父亲的安全,什么条件都可以谈。索拉索笑了,
露出一口黄牙。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聪明人打交道,迈克尔。汽车在餐厅门口停下。
这里灯光昏暗,顾客寥寥,空气中飘着大蒜和番茄酱的味道。我被搜了身,
确认没有携带任何武器后,才被带到一张靠墙的桌子前。晚宴开始了。
索拉索和麦克劳斯基大声地谈笑着,用蹩脚的意大利语点着菜,仿佛已经胜券在握。
我低着头,默默地切着盘子里的牛排,感受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我在等,等一个信号。
当窗外传来一阵熟悉的、越来越近的轰鸣声时,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那是高架铁路上火车经过的声音。我想……去一下洗手间。我放下刀叉,
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自然。麦克劳斯基警惕地看了我一眼。索拉索则挥了挥手,
示意他不必紧张。我站起身,双腿有些发软。走向洗手间的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
我能感觉到背后那两道审视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跟随着我。关上洗手间的门,
我背靠着冰冷的门板,大口地喘着气。镜子里,映出了一张苍白而陌生的脸。那是我吗?
那个曾经在战场上拯救战友,发誓要远离家族罪恶的迈克尔·科莱昂?我没有时间犹豫。
我伸手探进马桶的水箱,冰冷的水浸湿了我的袖口。我的指尖,
触碰到了一个同样冰冷的、用胶带缠绕的硬物。是枪。我把它拿出来,撕掉胶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