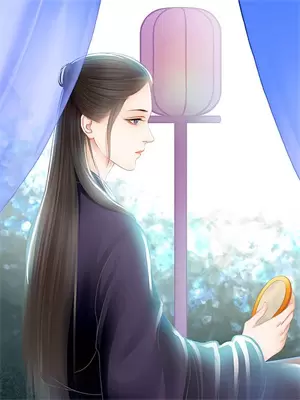雨像一层密不透光的帘子,敲在窗檐与防盗网之间,发出密集的金属颤音。凌晨两点五十七分,手机屏幕忽然亮起,一条取件短信从黑暗里弹出来——
您的包裹已放至门口。
林知远盯了几秒,像是从梦里被拽出来。他没有开灯,拖鞋踩过木地板,木纹在潮气里轻轻呻吟。猫眼外,楼道的感应灯一闪一灭,远处有水沿着楼梯扶手滑落,滴声像脉搏。
门一开,冷湿的风挤进来。门口放着一个灰白纸箱,边角已经被雨浸软,纸板起了毛。快递单上显示的寄件人空白,只有一串不完整的地址:祁宅·镜屋区。
他怔住——这两个字像有人在脑子里敲了一下。他知道“祁宅”,十年前的新闻里烧成黑洞的那栋别墅;也是他母亲失踪前最后一次被目击的地点。
指腹在快递胶带上划过,皮肤与塑料摩擦发出细碎的刺声。他把箱子拎进来,随手关门。屋里还保持着他工作的温度:桌上散了一摞关于镜像理论的论文与病理案例,曲别针像小爪钩在纸角。窗外的雨打成片,黑得像无穷无尽的镜面。
箱子里有两样东西:一张厚纸卡片,黑底银字;一台老式相机,皮质机身,磨损的边缘透出金属的冷。
纸卡像一张门票。上面印着——
镜屋入场券 时间:任一夜雨夜尤佳 人数:限定受邀者 备注:携带相机
卡片的边缘压着一道暗红的渗痕,像指腹按下去才印出来的血线。背面没有字。他把卡片放在桌上,手指却在纸面上停了停,指腹感到一种极轻的凹凸。像是有字被压在里面,只是被涂层掩住。
林知远走向窗边,窗上凝着一层雾。他想起一个老游戏——在玻璃前呼气,隐形墨水会浮出来。他把卡片举到唇边,吐出一口热气。白雾从纸面滚过,一行细细的字像被河水冲洗后浮出河床:
你欠我的影子,还我。
他心头一凉,连带胃也紧了一下,仿佛里面有根线被突然收紧。他抬头看窗,窗里的自己也在抬头看窗。除了那双眼睛显得比平时更黑,没什么异样。
老相机静静躺在箱子的褶皱里。皮带上有干涸的盐迹,像是从某些潮湿的夜里带回来的。他把相机拿出来,重量比看起来更沉。机背上的小小取景窗像一个始终张开的黑眼。快门很久没被按过,但一推拨杆,齿轮竟然顺畅地运作,像有人刚维护过一样。
他举起相机,对准墙上斜挂的时钟。透过取景窗,时钟的秒针在二与三之间,卡着不动;然而现实里的秒针正沿着刻度往前走。林知远的眼睛微微眯起,再对准桌角那盏落地灯,灯在现实里还没开,取景窗里却亮起一团微弱的黄。
他放下相机,低低地骂了一句。理性在工作——老旧相机镜片潮夜起雾,造成光差;或是镜片镀膜老化,反射出残留光印。解释就像栓在他脑子里的安全绳,他需要它。
但那根绳突然松了一下。
他再次举起相机,转向自己,镜头对准自己的脸。他看着取景窗里的自己:无光、无笑、眼下有黑得过分的影。他移动了一下嘴角,现实里的他没有笑,取景窗里的他——先笑了一下,嘴角缓慢上扬,露出整齐的牙,笑容延迟而僵硬。过了半秒,现实里的嘴角才仿佛被某种看不见的线拉扯一般,跟着上扬,像在补动作。
他把相机放下,呼吸在喉头绊了一下。雨声像被调大了音量,滴水在楼道里击中某个金属桶壁,咚、咚、咚,慢得像心跳。
手机震了一下。他以为是平台的论文提醒,解锁。弹出的却是一个陌生号码的彩信。信里只有一张照片——从他家门口视角拍的门缝,黑里透出一条缝隙光。时间标记是刚刚两分钟前。
他下意识地看向门,门锁完好,门缝细如一线。心里那根细线又被扯了一下,这次扯到了背脊。他打开手机相机,点开前置,画面里是他微微垂着肩的影子以及背后窗外密密的雨。他盯着屏幕里自己的脸,想确认那“延迟微笑”是不是错觉。
屏幕里的他先眨了一下眼。
现实里的他还没眨。下一秒,眼皮像被提醒了什么似的,才慢吞吞地合上又抬起。那一瞬间的错位像一根细针,从眼白刺进脑子,加上天花板的冷光,把一切都化成了尖锐。
他猛地把手机放下,喉结滚了一下,汗从后背渗出来。这是错觉。他对自己说。他研究过视觉延迟,也知道人在紧张状态下会把先入为主的影像误以为现实。他往后退了一步,脚踝撞上了椅脚,椅子被推得吱呀作响。
屋里安静得过分,只有雨声像无数微小的手指敲打着玻璃。桌上的“入场券”在空调风口的气流里微微颤动,金属压痕闪烁了一次,像有一只平整而锋利的舌在纸背滑过。
林知远把相机重新举起,这一次他把取景框对准了门。木门上贴着搬家的时候留下的透明缓冲保护膜,某个角落已经起翘,边缘卷起一层白。他慢慢推进焦距,门板的纹理变得像树的年轮,一圈一圈,在光下发出潮湿的光泽。
取景窗里,门缝并不完全是黑的。黑里有一块略浅的形状,像人的侧脸轮廓——鼻梁、眉骨与超出常理的笑线。那笑线太长了,从嘴角贴着脸颊一直延伸到耳垂。
他没有放下相机。这次他做了一个更直接的动作:右手竖起食指,轻轻在自己唇边点了一下。现实里的手指刚触到唇角,取景窗里的“他”已经把食指压着双唇,笑了一下。顺序又反了。
反了。这个词像带了温度,烫着他。他突然意识到一个细节:相机的皮带在他手背上轻轻拂动,不是因为他的动作,而像是有人从另一头拉了一下。
他把相机放在桌上,走向门,贴上猫眼。楼道灯熄了,黑里只有安全出口的应急绿灯在尽头闪了一次,转角处不时有水滴下来,滴在楼梯中间那块铁板上,铛地一声,薄薄地回响。猫眼里没有人,只有来自楼下某户门口风铃的微颤。在这种雨夜,风铃每摆一下都像是有人用指尖轻轻碰了碰。
他没有开门。理智逼他做一个更“科学”的确认:换设备。他回到客厅,打开电脑前置摄像头,将屏幕分成两半,一边是电脑前置,一边是手机前置。两边的画面里同时是他的脸。他试着举起左手——
电脑前置里,他的左手滞后了半拍;手机里,他的左手提前了半拍。两块屏幕上的“他”像两架走错步的钟,只在某一瞬间达成统一,又立刻分叉。
雨又大了一些,隔着窗帘能感到水气的重量。他想起童年的一个画面:院子里挂了许多洗好的被单,风从里面吹过,人走在其中就像走进一间由布做的房子。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布后面站着什么人。母亲在那里面喊他名字,声音越来越远,他转身,看到白布上贴着自己的影子,影子的嘴在动,但声音不是从影子那里来的。
他打了个寒颤。他强迫自己把注意力从记忆里拉出来,落在桌上的“入场券”上。你欠我的影子,还我。这句话像在纸里发热。可他欠谁的影子?他从来不相信这些,他靠的是统计学与症候分析活着——他看过多少以“集体暗示”“镜像引导”作祟的案例?每一个人都以为“鬼先动了”,其实是自己在延迟。
他去卫生间,打开镜前灯,灯光在白瓷砖上炸开。镜子有一点雾,边角有老旧的黑点。他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努力让呼吸平稳。手伸进冷水里,捧了一把,水从下巴滴下,落在洗手台边缘的石纹上。
他把手机举到脸前,打开前置。屏幕里的他与镜子里的他齐齐对着他。三个“他”在狭小的卫生间里排成一条线。林知远一只手提着手机,一只手抹掉镜面上的雾。水珠在玻璃上拖出透明的尾巴。
“没事。”他对自己说。他试图笑了一下,给自己的肌肉下达指令。
镜子里的他没笑。手机屏幕里的他——先笑了。笑容从一侧脸颊缓慢升起,像有线把皮肤往上提。紧接着,镜子里的他也笑了,慢半拍;最后,现实里的他才感觉到嘴角被某种看不见的缝线牵引,机械地跟上那道弧。
滴——卫生间的灯轻微地闪了一下。雨声在那一瞬被压低,像有人按了遥控。林知远盯着屏幕,喉咙有东西要往上涌。屏幕里,“他”笑着,眼睛突然眨了一下——只有屏幕里的他眨了。镜子里的没眨,现实里的他也没眨。过了半秒,镜子里的他眨了;再过半秒,现实里的眼皮才艰难地合上又抬起。
三次眨眼,像三把细小的剪刀,咔、咔、咔,把什么东西一点点剪开。
他把手机拿远了一点,手指在屏幕上颤了一下,像是想把“自己”的脸捏小。他忽然发现前置镜头的上缘——也就是屏幕黑色的刘海边,贴着一道几乎看不见的浅红,像某人的指腹刚刚在那道黑边划过,留下了薄薄的血。他什么都没动——但手机里的“他”慢慢抬起了手,食指抵在嘴唇上,做出一个“嘘”的手势,笑容僵硬而周到,像礼仪。
这时候,客厅里传来一声轻响:啪。像纸卡片从桌面滑落地板。林知远没回头,他盯着手机,喉头微微滚动了一下——然后他看见,屏幕里的“他”,在把手指按在唇上之后,缓慢地、节奏奇怪地,朝他眨了一下。只眨了一次。
现实里的他,眼睛一动未动。冰冷从脚底往上爬,沿着小腿、脊柱、肩胛,把他舌根压得发麻。他能听见自己的心跳被拉长、拉长——**咚……咚……**像楼道里那只金属桶壁再被雨滴撞一下。
手机屏幕忽然黑了一瞬,又亮起。亮起的时候,前置画面没有了,他看到主屏。通知栏弹出一条新消息,来自未知号码,预览一行字:
“别回头。”
卫生间门外,黑暗像水一样在门缝边密集起来,听得见客厅里那张“入场券”在地面上被风沿着纸边吹动,擦、擦,像细针在皮肤表面来回试探。
林知远拿着手机,屏住气,手指缓慢地滑到摄像头图标上。他没有回头。他只把手机举高,对准了自己身后那一小条门缝。
屏幕里的黑更深一点,然后,一只几乎透明的指尖从黑里伸出来,轻轻点了一下屏幕上方的镜头——
画面震了震,自动对焦。前置镜头在无声里先眨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