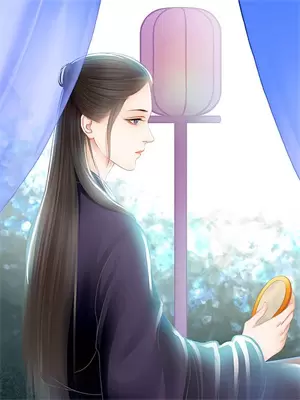前言:母亲头七那晚我违规烧了纸,灰烬中竟浮现她狰狞人脸厉喝:“谁让你烧的?
”第二天全家离奇暴毙,尸身围成圈,中央一堆灰烬显示下一个是我的名字。
---七月十五,阴雨刚歇,潮湿的土腥气和纸钱焚烧后特有的呛人味道混杂在一起,
沉甸甸地压在林家大宅的夜气里。林守站在后院墙角那片被雨水打得更显深褐的地面上,
最后一叠黄纸在他手里蜷曲、焦黑,化作明灭不定的橘红色火焰,再委顿成灰白的碎片,
随着热气袅袅升腾,飘摇几下,又无声无息地落回地面。白天的喧嚣和压抑的悲戚终于散尽,
只剩下死寂。母亲头七,规矩多得压死人,长辈们反复叮嘱过,今夜绝不能烧纸,煞气重,
易惹不该惹的东西。但他还是来了。心里堵得慌,那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愧疚和钝痛逼着他,
非得做点什么。仿佛这点微弱的光和热,能穿透阴阳,让母亲知道,他想她,
他悔——悔那天早上为什么偏偏和她吵那一架,悔没能见上最后一面。火焰舔尽纸边,
最后一点光亮挣扎着熄灭。夜风掠过墙头,带来一阵透骨的凉。
他盯着地上那摊尚有余温的纸灰,心里空落落的。就在这时,
那堆灰烬毫无征兆地猛地向内一缩,像是被地底无形的嘴吸了一口,
紧接着又诡异地膨胀、凸起!林守骇得倒退一步,脊背瞬间爬满白毛汗。纸灰翻滚,
簌簌作响,竟在他眼前凝聚、堆叠,勾勒出一张脸的轮廓——扭曲、变形,
边缘不断有灰烬剥落,又不断有新的补充上去,但那狰狞的眉眼,紧咬的牙关,
分明就是他逝去母亲的脸!灰烬构成的面孔剧烈抖动,仿佛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和愤怒。
下一瞬,一声尖厉到不似人声的咆哮,穿透夜间的死寂,狠狠凿进他的耳膜:“谁让你烧的?
!!”声音嘶哑破裂,裹挟着滔天的怨毒,根本不是母亲平日温婉的嗓音!林守魂飞魄散,
一屁股跌坐在冰冷的泥地上,手脚并用地向后猛蹭,直到后背重重撞上冰冷的院墙,
退无可退。他浑身抖得像是风中的残叶,牙齿格格打颤,
眼睁睁看着那灰烬人脸在吼出那一句后,骤然崩塌,散落回一地寻常的灰白,再无一丝异状。
夜风依旧呜咽,穿过廊下。仿佛刚才那恐怖的一幕,仅仅是他悲痛过度产生的幻觉。
他在墙角蜷缩了不知多久,四肢百骸都冻得僵透了,才勉强找回一丝力气。
连滚爬爬地逃回自己房间,反锁上门,一头钻进被子,蒙住脑袋,
彻骨的寒意却从骨头缝里往外渗。那一夜,他瞪大着眼,耳边反复回响着那可怖的厉喝,
ightest sound outside the window都能让他惊跳起来。
天亮时分,他才在极度的疲惫和恐惧中昏昏沉沉地睡去。没过多久,
一阵急促到疯狂的拍门声和尖叫声将他硬生生从混沌的噩梦中拽了出来!“守哥儿!守哥儿!
不好了!出大事了!!开门啊!”是管家福伯的声音,带着哭腔,嘶哑得变了调。
林守的心猛地一沉,不祥的预感像冰冷的巨手攫住了他的喉咙。他跌跌撞撞地冲下床,
拉开房门。福伯面无血色,浑身抖得如同筛糠,手指哆哆嗦嗦地指着前院的方向,
话都说不利索:“死……死了……全……全死了……”林守脑子里“嗡”的一声,
什么也顾不上了,一把推开福伯,发疯似的朝前院冲去。宅子里死寂得可怕,
下人们远远聚在通往前院的月亮门附近,个个面无人色,抖作一团,没人敢上前,
也没人敢出声,只有压抑不住的抽泣和牙关相击的咯咯声。林守冲进前厅——空的。
冲进偏厅——也是空的。一种令人窒息的恐惧感紧紧包裹了他。
他猛地转向通往父母居所的内院。内院的门敞开着。浓烈到令人作呕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几乎凝成实质。然后,他看到了。院子中央,青石板铺就的地面上,
用某种暗红色的、粘稠的液体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大圈。
他的父亲、继母张氏、大哥林伟、二哥林杰、大姐林芳、小妹林薇……全家七口人,
一个不少,全都躺在圈里。他们的身体以一种极度不自然的、扭曲的姿势摆放着,头朝内,
脚朝外,紧密地围成了一个圆圈。每个人的眼睛都惊恐地圆睁着,瞳孔放大到极致,
凝固着生命最后一刻看到的极致恐怖。脸上肌肉扭曲,嘴巴大张,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致命的伤口都在脖颈上,深可见骨,皮肉翻卷,
那暗红色的、几乎发黑的血液就是从那里流淌出来,浸透了他们的衣衫,
染红了身下的青石板,并且……勾勒出了那个将他们所有人串联起来的、诡异的圆圈。
林守的胃部一阵剧烈翻搅,他猛地弯腰干呕起来,眼泪鼻涕糊了满脸。他浑身脱力,
膝盖一软,跪倒在冰冷的石阶上,视线模糊地投向那死亡圆圈的中心。圆圈的正中央,
有一小堆灰烬。像是刚刚焚烧过什么,颜色比昨晚他烧的纸钱灰要深,近乎墨黑。
那些灰烬并非散乱无章,而是诡异地聚拢着,
勾勒出几个清晰的、令人头皮炸裂的字迹——那是一个名字。是他的名字。“林守”。
黑色的灰烬,凝固的鲜血,扭曲的尸体,惊恐的瞳孔,
的血腥和一丝若有若无的、纸钱焚烧后的焦糊味……所有的一切交织成一张巨大而恐怖的网,
将他死死缠在中央。他僵在原地,血液仿佛瞬间冻结,呼吸停滞,
连心跳都似乎被那无形的恐怖掐灭。下一个……是他?嗡鸣声占据了他的大脑,
世界在他眼前扭曲、旋转,最终归于一片绝望的漆黑。他向前一栽,失去了所有知觉。
……意识像是沉在冰冷粘稠的泥沼底部,挣扎着,一点点上浮。率先恢复的是嗅觉。
那股浓郁得化不开的血腥气,还有一丝冷冽的、属于夜雨的潮湿味道,钻入鼻腔,
刺得他太阳穴突突地跳。林守猛地睁开眼。视野先是模糊了一瞬,随即清晰。
他发现自己躺在内院冰凉的青石地上,离那个由至亲尸体组成的恐怖圆圈仅几步之遥。
父亲暴突的双眼正对着他,凝固的惊恐直刺灵魂深处。他连滚带爬地向后缩,
后背抵住廊下的红漆木柱,冰冷的触感让他打了个激灵,却无法驱散那彻骨的寒意。
胃里空空如也,只能发出一阵阵痉挛性的干呕。死了…都死了……除了他。为什么?
就因为昨晚……那叠纸钱?那句厉喝?“谁让你烧的?!
”母亲那狰狞的、由灰烬组成的脸孔又一次在他眼前浮现,
那嘶哑破裂的咆哮狠狠撞击着他的耳膜。恐惧像藤蔓一样勒紧了他的心脏,
但在这灭顶的恐惧之下,一股微弱却执拗的念头破土而出——为什么?凭什么?!
他不知道自己在那里瘫坐了多久。
直到院外传来压抑的哭泣和嘈杂的人声——大概是终于有胆大的邻居或报了官,官差来了。
凌乱而沉重的脚步声迅速逼近。几名穿着皂隶公服、腰佩铁尺的官差冲进内院,
领头的是个面色沉肃、眼神锐利的中年人,大概是捕头。即便他们见多识广,
在看到院内惨状的那一刻,也齐齐倒吸一口冷气,脸上血色尽褪,
有年轻的差役当场就扭过头去呕吐起来。“封锁现场!闲杂人等都退出去!
谁也不准碰任何东西!”捕头强自镇定,厉声喝道,声音却也有些发紧。
他的目光如鹰隼般扫过全场,迅速落在了唯一幸存的、瘫软在柱子旁的林守身上。
两名官差上前,粗鲁地将林守拖拽起来。他的手脚仍是软的,几乎无法站立。“是你发现的?
”捕头走到他面前,目光审视着他惨白如纸、失魂落魄的脸。林守张了张嘴,
喉咙干涩发不出声音,只能僵硬地点头。“家里还有谁?昨晚可有什么异常?
你最后见到他们是什么时候?”捕头的问题连珠炮似的砸过来。
“没…没了…都…都在那了…”林守的声音嘶哑得像是砂纸摩擦,
“我…我昨晚…睡得很死…什么…什么都没听见…”他下意识地隐瞒了烧纸的事情。
那太诡异,太难以启齿,说出来谁会信?只怕立刻就会被当成失心疯的凶手抓起来。
捕头眯起眼,显然不信,但看他抖得如同秋风中的落叶,状态极差,便暂时没再逼问,
转而吩咐手下:“仔细搜!查看所有房间,有无闯入痕迹,有无遗漏线索!仵作呢?!
快叫他进来验尸!”官差们立刻分散开来,如临大敌般开始搜查。林守被带到一边看管起来,
他抱着头,蜷缩在角落,听着官差们压抑的惊呼和仵作验尸时沉闷的声响,
胃里一阵阵翻江倒海。“……无明显外伤,
除了脖颈…”“……死亡时间大致在子时到丑时之间…”“……血迹分布奇怪,
像是死后被移动摆放…”“……这圈…是用血画上去的…”断断续续的话语飘进耳朵,
每一个字都让他冷彻骨髓。突然,一个在屋内搜查的官差捧着一个东西快步走出来,
脸上带着惊疑不定的神色:“头儿!您看这个!”那是一个铜盆。边缘有些磕碰,
是家里常用的那种。但此刻,盆底却残留着一层薄薄的、黑灰色的灰烬,
和院子中央那堆写着名字的灰烬极其相似!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那铜盆上,
然后又齐刷刷地投向院中央那堆灰烬,最后,落到了林守身上。
捕头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如刀,一步步走到林守面前,声音压得极低,
却带着巨大的压迫感:“这盆里的灰烬,是怎么回事?”林守的瞳孔猛地收缩,
心脏几乎跳出胸腔。他认得那个盆,那是他昨晚偷偷拿去后院烧纸用的盆!
“我…我不知道…”他声音发颤,避开捕头逼视的目光,
“可能就是…平常烧点废纸…”“平常烧废纸?”捕头冷笑一声,猛地伸手指向院子中央,
“那这个呢?!那堆灰烬里写着的名字,你怎么解释?!林守!”最后两个字,
他几乎是吼出来的,震得林守耳膜嗡嗡作响。“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林守崩溃地大叫起来,恐惧和绝望淹没了他,“我醒来就是这样!我什么都不知道!
”“带走!”捕头不再听他辩解,厉声下令。如狼似虎的官差立刻上前,
铁钳般的手抓住他的胳膊,将他向外拖去。林守奋力挣扎,嘶喊着“不是我”,但无济于事。
经过院子时,他眼角的余光再次瞥见那圈尸体,瞥见中央那黑灰的“林守”二字。
就在他被拖出内院月亮门的那一刻,一阵阴风突兀地卷起,打着旋吹过院中央那堆灰烬。
黑色的灰烬被风扬起,纷纷扬扬,却没有散开,反而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拨弄着,
微微改变了些许形状。那原本清晰的“林守”二字,边缘的笔画似乎蠕动了一下,
变得……更加尖锐了一些。捕头的目光一直死死盯着那堆灰烬,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异常,
眉头紧紧锁起。而林守,在被拖离这人间地狱的最后一瞬,心脏骤然缩紧,
一股比死亡更冰冷的预感,毫无缘由地攫住了他。那东西…还没完。那阵阴风卷起的灰烬,
像黑色的毒虫,在他视网膜上短暂地烙下更显尖锐的笔画痕迹,
随即被拖拽着他的官差粗暴地扯出了月亮门。“放开我!那东西还在!你们看不见吗?!
”林守嘶哑地吼叫,试图扭回头去看,但官差的手像铁箍,毫不留情地将他往外推搡。
“少装神弄鬼!有什么话,回衙门再说!”押解他的差役满脸不耐,
眼神里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惧。林家大宅的惨状,任谁看了都会做噩梦。
前院围观的仆役和闻讯赶来的邻里被官差们拦在外围,一道道目光钉在他背上,
惊恐、怀疑、幸灾乐祸……种种情绪交织成一张密实的网。
剩他一个……”“……怕是撞邪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啊……”这些话像冰冷的针,
扎进他混沌的脑海。他不是凶手!可谁能证明?那盆灰烬,那个名字……所有证据都指向他。
还有昨晚……母亲那狰狞的灰烬面孔和厉喝……他死死咬住牙关,
将那几乎要冲口而出的诡异经历强行咽了回去。不能说,说出来,只会被当成疯子,
更快地定罪。他被粗暴地塞进一辆等候在宅门外的囚车。木栅栏关上,落锁,
发出沉闷的声响。透过栅栏缝隙,
他最后看了一眼生活了二十年的家宅——朱漆大门上白色的封条交叉贴着,
在阴沉的天空下显得格外刺目。血腥味似乎穿透了高墙,弥漫在空气里,引来了几只乌鸦,
在不远处的枯树枝头哑声叫着。囚车颠簸着驶向县城衙门。一路上,无人说话,
只有车轮碾过石板的咕噜声和官差沉重的脚步声。林守蜷在囚车一角,身体冰冷,
内心的恐惧却在疯狂滋长。不是因为衙门,不是因为可能的刑罚,
而是因为母亲那张灰烬组成的脸,因为院中那圈尸体,
因为中央那诡异地改变了一丝笔画的他的名字。下一个……是他。
这句话在他脑子里疯狂回荡,像催命的符咒。衙门偏堂,灯火通明,却更添阴森。
县令是个面色焦黄、留着山羊胡的中年人,此刻眉头紧锁,看着跪在堂下的林守,
又看看摆在面前作为证物的铜盆,以及仵作匆匆送来的初步尸格笔录。“林守,
”县令声音沉缓,带着惯有的威严,“你一家七口,一夜之间尽数惨死,
现场唯有你一人存活,院中灰烬写你姓名,烧纸的铜盆亦是从你房中搜出。你作何解释?
”“大人明鉴!”林守重重磕头,额头抵着冰冷的地砖,“学生昨夜因母亲头七,心中悲恸,
确在后院墙角烧了些纸钱寄托哀思,但绝未杀害家人!学生回房后便昏睡过去,
直至被管家叫醒,才发现……发现惨案!学生手无缚鸡之力,如何能杀害全家?
更何况那是学生的至亲啊!求大人明察!”他避重就轻,绝口不提灰烬显灵之事。“至亲?
”旁边的师爷冷哼一声,阴阳怪气地开口,“据邻里反映,
你与你继母张氏及其所出子女素来不睦,前几日还因家产分配之事与你父亲发生过激烈争吵,
甚至有人听闻你放话‘迟早要让他们好看’,可有此事?”林守身体一僵。确有争吵,
但他从未说过那种话!是有人栽赃!“大人!那只是寻常口角,学生绝无杀心!更何况,
大哥大姐他们……”他想说大哥大姐与他关系尚可,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在这种情境下,
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寻常口角?”县令猛地一拍惊堂木,
“寻常口角会闹到满城风雨?会让你在头七之夜违禁烧纸?林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