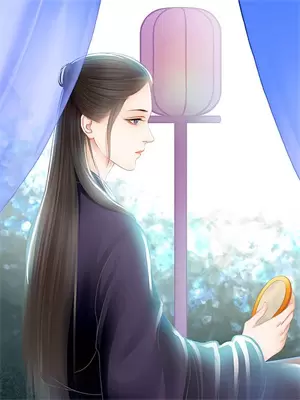前言: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失手杀死最好的朋友,
直到他腐烂的尸体开始每天出现在我家餐桌前,微笑着问我:“今天的饭菜合胃口吗?
”警方认定我有重大嫌疑却苦无证据,而真正令我崩溃的是,
今早那具尸体居然递来一张我们童年合影:“还记得谁真正失手了吗?”---雨声。
先是细密地敲打窗棂,继而变得瓢泼,冲刷着玻璃,混着夜里昏黄路灯的光,
扭曲成一道道蜿蜒的泥水。城市沉入一种被浸泡的寂静里,只有这无止境的雨声充斥一切。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已经忘了时间。空气里有一股味道,若有若无,我拼命嗅着,
想确定那不是真的,但那味道固执地钻进来——甜腻的,
带着铁锈和某种无法形容的腐败气息,像一块肉在盛夏闷热的角落里放了太久。
是从哪里来的?厨房的垃圾?还是…别的地方?冷。刺骨的冷。我裹紧了毯子,
牙齿却忍不住磕碰。不是因为雨夜的寒,而是从骨头缝里,从心脏最深处渗出来的寒意。
我的视线无法控制地、一次又一次地瞟向餐厅的方向。黑暗在那里浓郁得化不开。
长方形的餐桌,几把椅子,餐边柜模糊的轮廓。空无一人。当然空无一人。
可我为什么总觉得,在那片黑暗里,坐着什么?记忆的碎片像玻璃渣一样翻滚切割。
昨晚…或者说,那无数个混乱昼夜里的某一个…灯光摇晃的房间,震耳的音乐,
林皓涨红的脸,我的怒吼,碎裂的酒瓶,刺眼的红…还有那一声闷响,以及之后,
沉重得令人窒息的寂静。不。不能想。我猛地站起来,跌跌撞撞冲进厨房,拧开水龙头,
用冰冷的水扑打脸颊。水流声暂时盖过了雨声,也冲散了那若有若无的腐臭。
我双手撑在水槽边,大口喘息,看着水流打着旋消失在排水口。抬起头,
镜子里的人脸色惨白,眼窝深陷,瞳孔里是无法掩饰的恐惧。这是我。张辰。
是我失手杀了林皓。我最好的朋友。这个认知像一把烧红的铁钎,
每一次想起都烙烫一次灵魂。我不是故意的,那只是一场失控的争执,
一次该死的意外…但错了就是错了。我处理了…处理了一切。没有人知道。只要我不说,
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警察白天来过了。两个男人,一个年长些,眼神平和但锐利,
姓陈;一个年轻,记录着每一句对话。他们问起林皓的去向,问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问我们是否有什么矛盾。我尽力表演着一个担忧好友的友人,
声音干涩地给出排练过无数次的答案。他们似乎没有全然采信,那种审视的目光,
几乎要剥开我的皮肤。但他们没有证据。我告诉自己,冷静,只要冷静,就能过去。
水龙头还在哗哗地流。我关上它。寂静瞬间回归,而雨声似乎也停了。太静了。
静得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咚,咚,咚,沉重得像敲在空木头上。然后,
另一种声音插了进来。非常轻微。嗒。像是金属轻轻碰在瓷盘边缘的声音。我的血瞬间凉了。
猛地转头,看向餐厅。黑暗里,一个轮廓缓缓浮现。就在我的餐桌主位旁,
那个原本空着的位置上,一个身影坐在那里。轮廓熟悉得让我心碎,又恐怖得让我僵直。
阴影覆盖着他,只能看清一个模糊的、深色的人形,像是在水里泡久了的那种肿胀的暗色。
他面前,似乎摆着一只盘子。那身影动了动,仿佛调整了一下坐姿。布料摩擦,
发出细微的窸窣声。然后,一个声音响起来。嘶哑,含混,像是声带被砂纸磨过,
又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每一个字都带着湿漉漉的、缓慢渗漏的粘稠感。
“今天的饭菜…”它顿了顿。“…合胃口吗?”我的呼吸停滞了。大脑尖叫着否认,
命令身体逃跑或者攻击,但四肢百骸被无形的冰封冻,连眼球都无法转动。胃袋抽搐,
喉头紧缩,那股腐烂的甜腻气味陡然变得无比浓烈,充斥了整个空间,几乎凝成实体,
压迫着我的每一次心跳。幻觉。是压力太大了。是幻觉!我死死闭上眼睛,指甲抠进掌心,
刺痛感传来。数秒,或者数分钟,我像个石雕一样站着。
直到那股令人作呕的气味似乎淡去了一点。我一点点,极其缓慢地,睁开眼。
餐厅依旧沉浸在黑暗里。空无一人。餐桌光滑的表面反射着窗外一点微弱的光,
那里什么都没有。没有身影,没有盘子,没有声音。冷汗顺着我的脊柱往下淌,内衣湿透,
贴在皮肤上,一片冰凉。我几乎是爬回客厅的,瘫软在沙发上,像一条离水的鱼般剧烈喘息。
恐惧稍退,留下的是更深重的虚脱和茫然。我看着那一片空旷的餐桌,心脏仍在疯狂擂鼓。
是幻觉。只能是幻觉。但那股味道…那声音…一夜无眠。天亮时分,雨终于停了。
阳光勉强穿透云层,给房间镀上一层灰白的光,非但没有带来暖意,
反而让一切显得更加苍白和虚假。警察又来了电话,例行公事地询问了几个细节,
语气听不出什么异常。我应付过去,挂断电话,手心全是汗。白天似乎安全一些。
我试图整理房间,试图吃东西,试图做任何能让生活看起来正常一点的事情。
但我的视线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向餐厅。那个空着的位置,像一个黑洞,
吸走了房间里所有的生气。夜幕再次降临。比前一天更深的恐惧攥住了我。
我开了家里所有的灯,让每一个角落都亮如白昼。我打开电视,把音量调到最大,
让嘈杂的人声和音乐驱散寂静。我蜷缩在沙发最中间,瞪大眼睛,拒绝睡眠。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电视里播放着无聊的午夜节目。突然。所有的灯,闪烁了一下,熄灭了。
电视屏幕也瞬间黑了下去。寂静和黑暗如同有生命的实体,猛地扑了上来,将我彻底吞没。
只有窗外极微弱的光,勾勒出家具模糊的轮廓。我的心脏跳到了嗓子眼。是跳闸?
还是…在那片深沉的黑暗里,在餐厅的方向,一点微光幽幽亮起。像是烛火。昏黄,摇曳,
只能照亮极小的一圈。光圈下,是那张餐桌。和坐在桌旁的身影。他比昨天更清晰了。
我能看清他身上穿的,正是那天晚上的那件深蓝色衬衫,现在那颜色变得污糟不堪,
紧贴在他肿胀的身体上。他的皮肤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灰败和浮肿,上面布满了深色的斑块。
他的头发湿漉漉地搭在额前。他微微低着头。烛光在他面前跳跃,餐桌上似乎摆着几盘东西,
看不清具体是什么,只是一团团模糊的深色,映着烛光,泛着油腻的光泽。我无法动弹,
无法发声,只能看着。恐惧像藤蔓一样缠绕我的脖颈,越收越紧。他慢慢地,极其缓慢地,
抬起了头。烛光照亮了他的脸。我的胃一阵翻江倒海,酸液涌上喉咙。
那已经不是林皓的脸了。肿胀、扭曲,五官的位置都似乎发生了移动。皮肤像是融化的蜡,
嘴唇咧开,露出过于密集的牙齿,颜色暗黄。最恐怖的是他的眼睛。那双眼睛没有焦距,
蒙着一层灰白的翳,却直勾勾地“看”向我的方向。他咧开的嘴角慢慢向上扯动,
形成一个绝对不属于人类的、极端诡异的微笑。然后,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更近了,
更清晰了,那股腐败的气息浓郁得让我窒息。“今天的饭菜…”他停顿了一下,
灰白的眼珠似乎转动了一毫。“…合胃口吗?”“啊——!!!
”我听到自己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尖叫,猛地从沙发上弹起来,不顾一切地向后缩,
撞翻了茶几上的杯子,碎裂声刺耳。我胡乱地挥舞着手臂,试图驱散那恐怖的幻象。“滚开!
滚开!你不是真的!你不是!”我语无伦次地嘶吼着,眼泪和鼻涕一起涌出。
那烛光摇曳了一下。餐桌旁的身影,连同那昏黄的光圈,像信号不良的电视画面,
闪烁了几下,倏地消失了。灯光骤然恢复光明,电视也重新响起声音。
刺目的光线让我瞬间失明。我瘫倒在地毯上,蜷缩成一团,浑身剧烈地颤抖,
呜咽声无法抑制地从喉咙里漏出来。不是幻觉。那绝对不是幻觉!它回来了。林皓回来了。
他知道是我,他来报复我了。接下来的日子,变成了无法形容的地狱。
警察的造访越来越频繁。陈警官的问题开始变得尖锐,带着陷阱。他们调查了我的车,
我的通讯记录, subtly地施加压力。我知道他们怀疑我,但他们找不到尸体,
找不到凶器,找不到任何直接证据。这场问询成了拉锯战。而比警察更恐怖的,
是每个夜晚的“聚餐”。他不再局限于餐桌。
有时我会在浴室镜子的水汽里看到他模糊的身影;有时一回头,他会站在走廊的尽头,
静静地“看”着我;有时在梦里,他会一遍遍重复那场致命的争执,然后凑近我的脸,
问我合不合胃口。他的状态一天比一天“新鲜”。最初的腐烂肿胀似乎在慢慢减轻,
变得越来越像…生前的他。只是那双灰白的、没有生气的眼睛和那诡异的笑容从未改变。
他的问题也永远是那一句:“今天的饭菜合胃口吗?”我快要疯了。我无法睡眠,无法进食,
体重急剧下降,眼神涣散,无法集中注意力。我对所有人都充满了戒备,
包括陈警官那双似乎能看透一切的眼睛。我生活在极致的恐惧里,
每一秒都在等待下一次“见面”,等待那句索命般的问候。我开始怀疑一切。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细节为什么开始模糊?我真的…只是失手吗?直到这个早晨。
阳光刺眼。我一夜未眠,头痛欲裂,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我摇摇晃晃走进餐厅,
想去倒杯水,却下意识地避开了那个主位的位置。他就在那里。阳光明媚,
透过窗户照在他身上,甚至给他周身镀上了一层不真实的金边。
他看起来几乎和生前的林皓一模一样,只是脸色过于苍白,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僵在原地,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麻木地看着他。来吧,问吧,问那句该死的话。
但他没有问。在明亮的光线下,他缓缓地抬起手。他的动作似乎比夜晚时流畅了一些,
却依然带着一种非人的僵硬感。他的手里拿着一张东西。一张旧照片。边缘已经发黄,卷曲。
他保持着那种固定化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微笑,将照片慢慢地、慢慢地推到餐桌对面,
正对着我的位置。他的声音响起,这一次,异常清晰,
甚至带上了一丝…熟悉的、属于生前的林皓的语调,然而混合着那种非人的冰冷,
显得更加怪异。“还记得吗?”他灰白的眼珠盯着我。“还记得谁真正失手了吗?
”我的目光无法控制地落下,聚焦在那张照片上。照片上是两个勾肩搭背的小男孩,
站在一棵高大的老槐树下,笑得灿烂无比,露出缺了门牙的牙床。一个是我。一个是林皓。
我们的童年合影。记忆的闸门被某种暴力猛地撞开,一个被我深埋了二十年的画面,
裹挟着尘土、阳光和血腥气,轰然冲入我的脑海!那棵老槐树!那个陡坡!
那个自制的、粗糙的木头手枪!争夺,嬉笑,假装的射击…然后,脚下一滑!剧烈的拉扯!
尖叫声!沉重的撞击声!
体…苍白的脸…还有大人赶来的脚步声…无边的恐惧…一个决定…“不是我…”我喃喃自语,
盯着照片上林皓那张天真无邪的笑脸,再缓缓抬起眼,
看着餐桌对面那个苍白、微笑的“人”。冰冷的、彻骨的寒意并非来自外界,
而是从我心脏最深处爆炸开来,瞬间冻结了血液,凝固了呼吸。
整个世界在我眼前扭曲、崩塌、化为齑粉。我的嘴唇颤抖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那双灰白的、没有生命的眼睛,正一眨不眨地,等待着我的答案。
那张发黄的照片静静躺在桌面上,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穿了我所有的认知。
阳光刺眼得残忍,把他——不,把它——照得纤毫毕现。
皮肤下甚至能看到淡青色的血管纹路,只是毫无生气,像精致的蜡像。可那笑容,
那凝固的、嘴角弧度精确上扬的笑容,比任何腐烂的状态更让我胆寒。它刚刚说了什么?
谁…真正失手?童年的老槐树,夏日的蝉鸣,土坡,
自制的木头手枪……那些被时间层层覆盖、几乎被我彻底遗忘的碎片,
被一股蛮力粗暴地掀开,劈头盖脸砸向我。争夺。嬉笑。脚下一滑。沉重的拉扯。惊呼。
撞击闷响。还有……石头上的……刺目的红……一个小小的身体软下去,那么安静,
脸白得像纸。不是我推的。是意外!是意外!大人跑来的脚步声,
慌乱的叫喊……无边的恐惧淹没了一个孩子……然后……然后……一个决定。
一个沉默的、延续了二十年的决定。我的视线死死钉在照片上,那两个没心没肺笑着的男孩,
他们的快乐隔着漫长岁月和此刻极致的恐惧,发出无声的嘲讽。胃里翻搅得厉害,
喉咙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餐桌对面,它维持着递出照片的姿势,灰白的眼珠一眨不眨,
那非人的微笑焊在脸上,像是在欣赏我的崩溃。空气凝固了。时间也死了。
只有我胸腔里那疯狂擂动、几乎要炸开的心跳,证明我还可悲地活着。
“不……”一个气音从我牙缝里挤出来,干涩得像是砂纸摩擦,
“不是……那只是意外……是你自己……滑倒了……”我的辩护虚弱不堪,
连自己都无法说服。记忆的潮水汹涌澎湃,试图冲垮我精心构建了二十年的堤坝。
它的头颅极其缓慢地歪了一下,发出极细微的、像是颈椎摩擦的“咔哒”声。
这个近乎孩童般疑惑的动作,出现在这样一具“东西”身上,令人头皮炸裂。“意外?
”它的声音又响起了,依旧是那种混合着生前后调与非人冰冷的怪异感,
每一个字都滴着粘稠的恶意,“那你为什么……跑了?
”“你为什么……告诉所有人……是我贪玩……自己摔下去的?
”“你为什么……二十年……都没说过真话?”它的语速平缓,没有质问的力度,
却像一把冰冷的凿子,一下一下,精准地凿开我记忆的硬壳,露出里面肮脏腐烂的内核。
我猛地向后退,椅子腿在地板上刮出刺耳的尖叫。我浑身抖得像是风中的落叶,视线模糊,
几乎看不清它的样子。“你胡说!你死了!你已经死了!”我歇斯底里地吼叫起来,
试图用声音压过内心的恐惧和……那疯狂滋长的、我不愿承认的罪恶感,“现在的你是假的!
是幻觉!是因为警察!是因为压力!滚!给我滚!”我抓起手边的一个玻璃水杯,
用尽全身力气朝着它砸过去。水杯穿透了它的身影,像是穿过一团全息投影,
砸在它身后的墙壁上,“砰”地一声碎裂,水渍和玻璃渣四溅。它的影像波动了一下,
像水面投入石子后的涟漪,但瞬间又恢复了稳定。笑容丝毫未变,
甚至……那双灰白的眼睛里,似乎掠过一丝极淡的、嘲弄的光。它慢慢抬起另一只手,
那只没有推照片的手,指向餐桌的另一侧,那把空着的椅子。“坐下,张辰。
”它的声音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冰冷。“我们……该吃饭了。”吃饭?吃什么?
那些在烛光下看不清的、泛着油腻光泽的深色团块?剧烈的恶心感冲上喉头,我干呕起来,
什么也吐不出,只有酸涩的胆汁灼烧着食管。就在这时,门铃响了。
叮咚——叮咚——叮咚——急促,连续,带着一种官方特有的不容置疑的味道。是警察!
陈警官!巨大的恐惧和一种扭曲的、近乎获救的冲动同时攫住我。我连滚爬爬地冲向门口,
几乎是扑倒在玄关,颤抖着手拧开门锁。门外站着的果然是陈警官和他那个年轻的搭档。
陈警官的目光一如既往的锐利,像鹰一样瞬间攫住我惨白的脸、满头的冷汗和失控的神情。
“张先生?你还好吗?”陈警官的眉头皱起,视线越过我的肩膀,试图看向屋内。
“他……他……”我语无伦次,手指胡乱地指向餐厅的方向,呼吸急促得像刚跑完马拉松,
“在那里!他又来了!就在那里!”陈警官和年轻警员交换了一个眼神。那种眼神我见过,
混合着怀疑、审视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又来了”的不耐。“谁在那里?
”陈警官的声音保持平稳,带着公事公办的冷静。“林皓!是林皓!”我几乎要尖叫出来,
“他坐在我家餐桌那里!每天都来!问我合不合胃口!他拿了照片!他说了以前的事!
他……”我的话戛然而止。因为我看到陈警官的眼神变了。那不是相信,
而是一种更深沉的、几乎是怜悯的探究。他在判断我的精神状况。
年轻警员甚至微微调整了一下站姿,手看似无意地搭在了腰后的装备上。“张先生,
”陈警官的声音放缓了些,像在安抚一个躁动的病人,“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我猛地让开身,几乎是祈求他们赶紧进去,用他们的眼睛证实我不是疯子,
证实那东西真的存在!两个警察走了进去,脚步沉稳,带着职业性的警惕。
我紧跟在他们身后,手指死死攥着自己的衣角,目光死死钉在餐厅入口。他们走进了客厅。
阳光充沛,一切无所遁形。餐桌旁。空无一人。只有那把椅子安静地摆在那里。
桌面上干干净净,除了我刚才砸碎杯子留下的一小滩水渍和远处墙角的玻璃碎片,
什么都没有。没有烛光。没有盘子。没有尸体。更没有那张该死的童年合影。
陈警官缓缓转过身,目光重新落在我脸上。他没说话,但那沉默比任何质问都更有力量。
年轻警员仔细检查了餐厅和客厅的连接处,甚至弯腰看了看餐桌底下,
然后对着陈警官微微摇了摇头。“不……不可能……”我喃喃自语,冲过去,
双手在空荡荡的餐桌上方胡乱挥舞,“他刚才就坐在这里!就坐在这里!他拿了照片给我看!
你们没看到吗?你们闻不到吗?那股味道!腐烂的味道!
”空气里只有清新的空气清新剂的味道,是我昨天刚买的,试图掩盖什么。
陈警官深吸一口气,走上前,拍了拍我的肩膀。他的手很稳,很有力,
却让我感到一阵刺骨的冰凉。“张先生,我想你需要休息。”他的声音很沉,
“你需要……专业的帮助。我们可以帮你联系……”“我不需要医生!”我猛地甩开他的手,
情绪彻底失控,“我需要你们抓住他!找到他的尸体!是他阴魂不散!是他不肯放过我!
他知道了!他什么都知道了!”“他知道什么了?”陈警官捕捉到我话语里的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