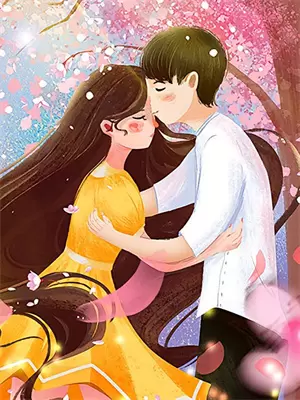后来啊,有人在江边捡到块刻着半朵梅的石头,有人在旧书里翻出晕开泪渍的字条。
原来有些爱,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沉进江底,烂在梅根里,却在岁月里发了芽,
长成一辈子的疤。林砚之头一回瞧见沈知珩,是在民国二十六年的深秋时节。彼时,
梧桐叶铺满了金陵城的石板路。她抱着刚从书局买到的线装书走出来,冷不丁地,
迎面就撞上了一个身着深色风衣的男人。这一撞,书散落得满地都是,
其中那本《白石词》的封皮,还被他皮鞋的边缘蹭出了一道浅痕。“抱歉。”男人一边说着,
一边弯腰去拾书。林砚之留意到,他的指腹带着薄薄的茧子,指尖擦过她手背的时候,
凉得就像落了片冰。她抬头望去,只见他眼底布满了红血丝,像是接连熬了好几个通宵,
但偏偏又生着一双极为明亮的眼睛,恰似寒夜里孤零零高悬着的星子。后来林砚之才知道,
沈知珩是中央大学的物理系教授,比她大七岁。
他常常在图书馆三楼靠窗的位置研读外文期刊,阳光斜斜地洒落在他的头顶,
能瞧见细碎的金色光芒。林砚之是国文系的学生,总爱找借口向他请教数学题,
其实不过是想听听他说话——他的声音就好像浸过雪水一般,冷冽中透着清透。
那年冬天来得格外早,第一场雪飘落的时候,沈知珩在实验楼后面的梅树下找到了林砚之。
当时,她正对着一枝含苞待放的绿萼梅出神,沈知珩走上前,递来一只手炉,
轻声说道:“林小姐,这里风大。”手炉带着温热,哪怕隔着羊毛手套,也能暖到心窝里。
林砚之想起昨夜在教授宿舍楼下,看到他房间的灯一直亮到凌晨,窗纸上映着他伏案的影子,
旁边还堆着厚厚的图纸。她不禁轻声问道:“沈先生在忙什么呢?”沈知珩微微顿了顿,
喉结动了动,回答道:“做点有用的事。”民国二十七年春天,战火步步紧逼金陵城。
学校无奈停课,学生们分批撤离。林砚之收拾行李的时候,
发现枕头下面多了一本《白石词》,正是沈知珩送的,
扉页上还有他留下的字迹:“江湖路远,各自珍重。”她心急火燎地跑到他的宿舍,
门虚掩着,屋内空无一人。桌上摊着尚未完成的公式推导,旁边压着一张纸条,
上面的墨迹十分潦草:“若遇战乱,往西南去,勿念。”在撤离的火车上,
林砚之挤在人群中间,怀里紧紧地揣着那本书。望着车窗外,金陵城的轮廓渐行渐远,
她突然想起沈知珩曾说过,他的故乡在北平,那里还有他瘫痪在床的母亲。辗转来到重庆后,
林砚之在一所临时中学教国文。日子过得清苦,防空洞成了她常去的地方。有一次,
轰炸来得又急又猛,她被倒塌的断墙砸中了腿,昏迷之前,
恍惚间似乎听见有人呼喊她的名字,那声音像极了沈知珩,却又好像不是。
等她在医院苏醒过来,腿上已经缠满了厚厚的纱布。护士告诉她,
是一位姓沈的先生把她送来的,留下这笔钱后就离开了。
林砚之摸索着拿出枕头下面的《白石词》,指尖轻轻抚过扉页上的字,
眼泪不由自主地掉落下来。到了秋天,她的腿伤已经好了大半。
林砚之听说沈知珩在兵工厂工作,便满心欢喜地揣着亲手织的毛衣去找他。
兵工厂位于郊区的山谷里,戒备极为森严。她在门口等了整整三天,
才终于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他明显瘦了许多,眼下的乌青愈发浓重,风衣上还沾着机油。
看到她的那一刻,他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皱起了眉头:“你怎么来了?”“给你送件衣服。
”林砚之把毛衣递过去,温柔地说,“天气眼看要冷了。”他却没有伸手去接,
声音冷得如同冰块:“林小姐,我们非亲非故,不必如此。”“沈先生,”她咬着嘴唇,
欲言又止。“我已有婚约。”他打断了她的话,眼神刻意避开她的目光,“是家里安排的,
等战事平息就成婚。”“你骗我的对不对……”林砚之手中的毛衣滑落至地,
毛线勾住了石子,绽开了一道口子。“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吧。
”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转身,大步走进大门,背影挺得笔直,
像一株被风雪压弯却不肯折的松。民国二十八年的冬天,重庆遭受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轰炸。
林砚之任教的中学瞬间被炸成了一片满目疮痍的废墟,她在这场灾难中幸运地捡回了一条命,
可那本无比珍视的《白石词》却在混乱之中遗失不见。林砚之像发了疯一般,
在残垣断壁的瓦砾堆里翻找。尖锐的碎玻璃划破了她的手指,
殷红的鲜血一滴一滴地落在洁白的雪地上,宛如一朵朵绽放得凄厉而又绝望的梅花。
就在这时,有人递过来一块手帕。林砚之抬起头,映入眼帘的正是沈知珩。他满脸都是灰尘,
左臂用布条简单地缠着,丝丝血迹正从里面渗出来。“别找了。”他的声音沙哑而疲惫,
“我再给你买一本就是了。”“不一样的。”林砚之泪流满面,拼命地摇着头,
“那是你送我的啊。”沈知珩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缓缓地从怀里掏出一个物件,
轻轻地放在她的手心。那是一枚被摩挲得十分光滑的玉坠,上面精心雕琢着半朵梅花。
“这个你拿着。”他目光坚定地说道,“等抗战胜利了,你去北平找我母亲,她有另一半,
你帮我合在一起。”林砚之紧紧地攥着那枚玉坠,望着沈知珩转身,
毅然决然地冲进了熊熊燃烧的火场,去营救那些被困的学生。
凶猛的火舌肆意地舔舐着他的风衣,仿佛要将他整个人都吞噬殆尽。这,
便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模样。后来,林砚之听闻,兵工厂出了内奸,
沈知珩负责的武器图纸不幸被泄露。在拦截特务的过程中,他身中数枪,
最终坠入了波涛汹涌的嘉陵江。直至最后,都没能找到他的尸身。抗战胜利的那天,
林砚之正身处北平的街头。整座城市都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鞭炮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然而,她却静静地站在沈知珩曾提及的那条胡同口,手中紧紧地握着那半枚梅花玉坠。
胡同的深处,有一座四合院,门半掩着。林砚之缓缓地走了进去,
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坐在轮椅上,正对着窗台上摆放的一盆绿萼梅出神。
“您是沈伯母吗?”林砚之轻声地问道。老妇人缓缓地转过头,
原本浑浊的眼睛里瞬间闪过一丝光亮:“你是……”林砚之轻轻地摊开手心,
那半枚玉坠在阳光下闪烁着温润的光泽。老妇人的手颤抖着,从怀里摸索出另一半玉坠。
当两块玉坠拼接在一起时,恰好组成了一朵完整无缺的梅花。
“知珩他……”老妇人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痛,泣不成声,
“他说要带个喜欢诗词的姑娘回来,说她笑起来像春天盛开的花……”直到此刻,
林砚之才恍然大悟。原来,沈知珩根本就没有什么婚约。
他在兵工厂从事的是最为危险的炮弹引信研发工作,每一天都徘徊在生死边缘,
随时都有可能失去生命。他之前说的那些绝情的话,不过是想让她彻底死心,
从此忘了自己罢了。老妇人递给她一个铁盒,告诉她这是沈知珩特意留下的。
林砚之打开铁盒,里面有几张她的照片,
都是沈知珩偷偷拍摄的——有她在图书馆专注看书的模样,
还有在梅树下踮起脚尖去够花枝的俏皮姿态。铁盒里还有一本日记,在日记的最后一页,
写着这样一句话:“若我身死,勿让她知。愿她一生安稳,不知人间疾苦。”窗外,
那盆绿萼梅正盛开得绚烂,清幽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清冽而又迷人。
林砚之轻轻地抚摸着那本日记,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到那年深秋。那时,他弯腰拾起书本,
指尖触碰她手背的温度,仿佛还停留在那一刻。自那以后,每年的冬天,
林砚之都会来到沈知珩消失的那段嘉陵江边。江水依旧滔滔不绝地流淌着,
它带走了悠悠的岁月,却怎么也带不走林砚之心中那道刻骨铭心的伤疤。她常常觉得,
沈知珩仿佛还活在这个世上,或许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看着这盛世如他所愿。
重庆的雨总带着股化不开的湿冷,黏在人骨头上。林砚之撑着油纸伞,
站在嘉陵江码头的石阶上,看浑浊的江水卷着枯叶往下游去。这是她来重庆的第三个月,
沈知珩“死”后的第十年。她是来收拾旧物的。兵工厂旧址早改成了仓库,
只有当年那片被炸过的瓦砾地还荒着,长出半人高的野草。
有人说在下游的渔村里见过个独眼的瘸子,手艺好,
尤其会修那种老式座钟——沈知珩以前就爱摆弄这些。雨丝斜斜打在伞面上,
溅起细碎的水花。林砚之转身要走,眼角却瞥见不远处的杂货铺门口,
一个男人正弯腰给顾客修伞。他穿着件灰布短褂,袖口磨得发亮,右腿明显不利索,
要靠手里的拐杖支着。背对着她时,后颈有道蜿蜒的疤,像条褪色的蛇,
在潮湿的空气里泛着青白。林砚之的呼吸骤然停了。她的伞“啪”地掉在地上,
雨水瞬间打湿了她的旗袍下摆。男人似乎听到动静,缓缓转过身。是他。
却又不是记忆里的模样。左眼眶覆着块发黑的棉布,右边的眉骨到颧骨,
一道狰狞的疤把曾经清俊的轮廓撕得支离破碎。他手里还捏着修伞的线,看见她时,
那只完好的眼睛猛地收缩,像被什么烫到,下意识就想往后躲,却因为腿脚不便,
踉跄了一下。“沈知珩……”林砚之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每一个字都像从喉咙里呕出来的,
带着血腥味。男人手里的线轴滚落在泥水里,他张了张嘴,喉结动了动,却没发出声音。
那只眼睛里翻涌着惊惶、痛苦,还有一种她看不懂的决绝,
像要把自己溺死在那片浑浊的光里。林砚之一步步朝他走过去。石板路湿滑,她走得很慢,
每一步都像踩在烧红的烙铁上。十年了,她在北平的梅树下等过,在嘉陵江的岸边哭过,
在他母亲的灵前立过誓,说要等他回来,哪怕是尸骨。可现在他就站在这儿,活生生的,
她却觉得心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着,疼得快要炸开。“为什么?”她走到他面前,
距离不过三尺,却像隔了万水千山。雨水顺着她的发梢往下滴,混着眼泪落在衣襟上,
“为什么不找我?”他低下头,看着自己残缺的手——左手的小指没了,
是当年被特务的子弹打掉的。“林小姐,你认错人了。”他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和记忆里那个清冷的声线判若两人。“我没认错!”林砚之猛地抓住他的手腕。
他的皮肤冰凉,骨节硌得她手心生疼,“你的疤,
你的手……”男人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他用力想抽回手,动作却因为激动而变得笨拙,
“放开!”他低吼着,那只眼睛里布满血丝,“我不是沈知珩!他早就死了!
死在嘉陵江里了!”“那我是什么?”林砚之的眼泪汹涌而出。“我这十年算什么?
守着一个空坟,没日没夜的想着你,念着你,等着你……”周围渐渐围拢了人,
指指点点的声音像针一样扎过来。男人的脸在雨水里显得愈发苍白,他猛地甩开她的手,
转身就想拄着拐杖走,却被她死死拽住了衣角。“你看看我啊!”她几乎是在哀求,
“沈知珩,你看看我!我是砚之啊!”他终于停下脚步,却没有回头。肩膀剧烈地起伏着,
像是在压抑着什么。过了很久,他才用那只完好的眼睛,透过雨幕,看向街角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