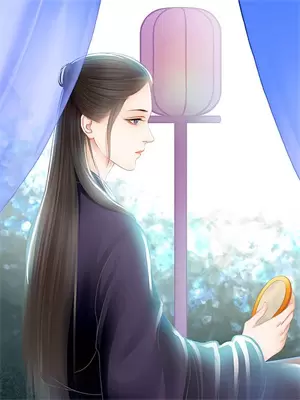1快递盒子不大,方方正正,上面没有寄件人信息,只有我的名字和地址,字迹娟秀,
像是出自一个女孩之手。我叫陈戈,一个半死不活的纸艺师,
守着市中心一条老街上快要倒闭的小店,
靠给一些公司做活动装饰或者给情侣做定制礼物勉强糊口。“谁寄的?”女友孙萌凑过来,
好奇地打量着。“不知道,可能是哪个客户吧。”我拿起美工刀,划开胶带。箱子打开,
里面没有泡沫,没有填充物,只有一只只叠得整整齐齐的千纸鹤。五颜六色,密密麻麻,
像一箱子绚烂的尸体。每一只都叠得极为精致,翅膀的角度,头部的弯折,
都像是用尺子量过一样,透着一种冰冷的精确。这绝对是出自一个高手,甚至比我更有耐心。
“哇,好漂亮!”孙萌拿起一只放在手心,“这是谁送的呀?还挺有心的。”我摇了摇头,
拿起一只血红色的纸鹤。纸张的质感很奇怪,不像市面上任何一种,韧性十足,
表面还有着极其细微的、如同皮肤般的纹理。我把它凑到耳边,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冲动。
我的听力从小就异于常人,能听到蚊子振翅的声音,能分辨出不同灯管发出的电流声。
这天赋让我饱受折磨,但也让我在纸艺这种需要极致安静和专注的工作里,找到了一丝安宁。
然而,就在纸鹤靠近耳朵的那一瞬间,一个冰冷、细微,几乎无法察觉的声音,
钻进了我的耳蜗。那是一个名字。“周浩……”声音像是一根冰针,扎得我一个激灵,
手里的纸鹤掉在了地上。“怎么了?”孙萌被我吓了一跳。“没什么,”我弯腰捡起纸鹤,
心脏却狂跳不止,“可能最近太累了,有点幻听。”我把箱子合上,随手塞到了工作台下面。
但那种被窥视的感觉,那种冰冷的恶意,却像是藤蔓一样,死死地缠住了我的神经。那一晚,
我失眠了。工作间里,那一箱纸鹤像是潘多拉的魔盒,无时无刻不在散发着不祥的气息。
我能“听”到它们,无数细碎的、重叠的、如同虫豸爬行般的声音,汇聚成一片混沌的噪音。
而在这片噪音之上,那个清晰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地在我脑海里回响。
“周浩……周浩……周浩……”我烦躁地用被子蒙住头,强迫自己不去想。周浩,
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好像是我初中的同学,一个很胖,总是笑嘻嘻的家伙。
毕业后就再也没联系过了。也许真的只是我太累了。第二天早上,
我是被孙萌的尖叫声惊醒的。她举着手机,脸色惨白地看着我,嘴唇都在哆嗦。
“陈戈……你看……你看新闻……”我接过手机,一条本地新闻的弹窗刺入我的眼睛。
“本市青年周浩于昨夜意外身亡,因在家中自行更换灯泡时意外触电,从梯子上摔落,
后脑着地,当场死亡。警方初步判定为意外事故。”新闻配图上,是周浩黑白色的证件照,
那张胖乎乎的笑脸,和我记忆里的样子一模一样。我的血液,在刹那间冻结了。
2“不可能……这只是巧合,对吧?”孙萌的声音带着哭腔,紧紧抓住我的胳膊,
仿佛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丝肯定。我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的喉咙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掐住,大脑一片空白。巧合?世界上有这么精准的巧合吗?
昨晚那个冰冷的声音,那个如同死亡预告般的名字,现在变成了一条冰冷的新闻。
我猛地推开孙萌,冲进工作间,发疯似的把那个纸箱子拖了出来。箱子很沉,
里面的纸鹤一只也没少。我把它们一股脑地倒在地上,五颜六色的纸鹤铺满了整个地板,
像一片诡异的坟场。我跪在地上,一只一只地拿起它们,凑到耳边。
大部分纸鹤都是“安静”的,只有那种细碎的、令人心烦的背景噪音。但我知道,它们之中,
一定还有“会说话”的。孙萌站在门口,惊恐地看着我,像在看一个疯子。“陈戈,
你冷静点!这不关你的事!只是个意外!”“不!不是意外!”我冲她吼道,双眼血红,
“你没听到!你什么都听不到!”我的听力天赋,在这一刻变成了最恶毒的诅咒。
只有我能听到死亡的预告,只有我被拖进了这个无边的恐惧深渊。终于,
在一只墨绿色的纸鹤里,我再次听到了那个声音。这一次,是另一个名字。
“李琴……”我的心沉到了谷底。李琴,我又想起来了,还是我的初中同学。一个戴着眼镜,
很文静,总是被周浩他们那帮人欺负的女孩。不,不对,被欺负的不是她。
她只是……只是站在旁边看着,从来不说一句话。恐惧像潮水般将我淹没。这不是随机的,
这是一个名单!一个死亡名单!而我,是唯一的听众。“我们得报警!”孙萌颤抖着说。
“报警?怎么说?”我惨笑一声,指着满地的纸鹤,“跟警察说,这些纸鹤会说话?
它们预告了周浩的死,现在又预告了李琴的?他们会把我们当成疯子关起来!”孙萌沉默了。
她知道我说的是事实。这种事,超出了所有人的认知。“那……那我们想办法联系上李琴!
提醒她!让她小心!”这是唯一的办法了。我翻箱倒柜,终于在阁楼一个布满灰尘的箱子里,
找到了那本早已泛黄的初中同学录。一页页翻过去,
我找到了李琴的名字和她当年留下的座机号码。天知道这号码还能不能用。
我用颤抖的手指按下那一串数字,听着电话里“嘟……嘟……”的忙音,
每一声都像是在敲击我的心脏。电话接通了。“喂?哪位?”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传来,
带着一丝警惕。“阿姨您好,我找一下李琴,我是她的初中同学,陈戈。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声叹息:“你……是陈戈啊。小琴她……她不在了。
”“不在了?她去哪了?”我心里咯噔一下。“她三年前就嫁到外地去了,我们也很少联系。
你找她有什么急事吗?”嫁到外地了!我的心稍微松了一下,只要她不在本市,
或许……或许能躲过一劫?“没什么急事,就是同学好久不见,想聚一聚。
”我勉强找了个借口。“唉,你们这些同学啊……算了,我把她手机号给你吧,
你们自己联系。”拿到手机号,我立刻拨了过去。电话响了很久,就在我以为没人接,
准备挂断的时候,终于被接起了。“喂?”一个怯生生的,有些沙哑的女声传来,正是李琴。
“李琴!我是陈戈!初中同学!你还记得我吗?”我急切地说道。“陈戈?
”她似乎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哦……记得。有事吗?”她的声音充满了疏离和疲惫。
“你听我说,不管你信不信,你最近一定要小心!千万别出门!特别是小心电!小心火!
小心一切可能发生意外的地方!”我语无伦次地喊道。电话那头,李琴沉默了。“陈戈,
你是不是打错了?”她的声音变得冰冷,“我们已经十几年没联系了。你大半夜打电话过来,
就是为了咒我死?”“不!不是的!你听我解释!”“嘟……嘟……嘟……”她挂了。
我再打过去,已经是忙音。她把我拉黑了。绝望瞬间笼罩了我。我该怎么办?我还能怎么办?
那一夜,我和孙萌谁都没睡。我们守着电话,守着新闻,像是在等待一场注定要来临的审判。
第二天,第三天,什么事都没发生。我和孙萌都松了一口气。也许,距离太远,
那个“诅咒”够不着她?也许,我的警告真的起了一点作用?我甚至开始怀疑,周浩的死,
真的只是一个巧合。然而,第四天早上,一条推送新闻,将我所有的幻想彻底击碎。
“我市一女子在家中被离奇烧死,疑为电热毯线路老化所致。”新闻里的配图,
是一栋被烧得漆黑的居民楼。而死者的名字,赫然是——李琴。报道说,
她是从外地回来探亲的。就在昨天晚上。
3.“她回来了……她竟然回来了……”我瘫坐在地上,嘴里反复念叨着这句话,
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孙萌在我身边泣不成声。这不是巧合,这绝对不是巧合。
死神就像一个精准的猎手,而那些纸鹤,就是它的死亡名单。李琴以为自己逃到了外地,
却没想到,她只是自己走回了屠宰场。恐惧已经不足以形容我此刻的心情,
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绝望。我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扼住了喉咙,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悲剧一个接一个发生,却无能为力。“陈戈,我们把这些东西烧了吧!
”孙萌指着那些纸鹤,眼神里充满了憎恶和恐惧,“把它们全都烧了!
也许……也许这样就能停下来!”烧掉它们?我看着满地的纸鹤,
它们在晨光下依然显得那么精致、无害。但我的听觉告诉我,它们的内部,
正涌动着令人作呕的恶意。“没用的……”我摇了摇头,声音嘶哑,“我试过了。
”就在李琴死讯传来的前一天晚上,我曾偷偷拿了几只纸鹤,
在楼下的垃圾桶里用打火机点燃。但诡异的是,那种特殊的纸张,根本点不着。火焰燎过,
连一丝焦黑的痕迹都没有留下。它们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东西,水火不侵。“那怎么办?
我们就这么等着?等着下一个名字出现?”孙萌崩溃地喊道。
下一个名字……我的心猛地一紧。我冲到那堆纸鹤里,再次跪下,像个疯子一样,
一只只地翻找,一只只地聆听。汗水浸湿了我的后背。那些细碎的、重叠的、恶意的低语,
像无数只蚂蚁在啃噬我的耳膜。我的精神正在被一点点地拖入崩溃的边缘。终于,
在一只惨白色的纸鹤里,我听到了。“王超……”这个名字一出来,我的手剧烈地颤抖起来,
那只白色的纸鹤掉在了地上。王超!他是我们初中时的班长,学习很好,但性格懦弱。
他也是周浩那帮人的欺凌对象之一,不,他比李琴更惨。周浩他们不仅抢他的钱,
还把他堵在厕所里,逼他学狗叫。而我,当时就在隔间里,我听到了所有声音,
听到了王超压抑的哭声和周浩他们肆无忌惮的嘲笑。我害怕得不敢出声,连呼吸都屏住了,
直到他们离开。我没有出去安慰王超,也没有告诉老师。我像个懦夫一样,溜走了。
这些尘封的、我刻意遗忘的记忆,此刻像是决堤的洪水,汹涌而出,淹没了我的理智。周浩,
霸凌的头目。李琴,冷漠的旁观者。王超,被欺凌的受害者。现在,轮到他了?为什么?
为什么他也是目标?这不合逻辑!除非……除非这个名单的制定者,
恨着当年与那件事有关的每一个人!无论你是施暴者,旁观者,还是……受害者。“找到他!
我们必须立刻找到王超!”我抓住孙萌的肩膀,用尽全身力气喊道。这一次,我不能再等了。
我不能再眼睁睁看着又一个人死去。我们再次翻出了同学录。王超当年留下的也是座机,
打过去已经变成了空号。我们开始疯狂地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但同名同姓的人太多了。
就在我们快要绝望的时候,孙萌突然在一个本地的骑行论坛里,
发现了一个叫“追风的阿超”的ID。他发的一张自拍里,那张瘦削的、戴着黑框眼镜的脸,
依稀还能看出当年王超的影子。找到了!根据他在论坛留下的信息,
他今天会参加一个环城骑行活动,上午九点,在城郊的湿地公园集合。我看了看表,八点半。
“来不及了!我们快走!”我拉起孙萌,冲出了家门。我们甚至来不及等电梯,
直接从楼梯往下冲。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阻止他!无论如何都要阻止他!
车子在路上飞驰,我把油门踩到了底。孙萌在一旁不停地打电话,
试图联系那个论坛的组织者,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八点五十五分,
我们终于赶到了湿地公园门口。公园很大,一眼望不到头。远处,
已经有一群穿着五颜六色骑行服的人聚集在湖边,看样子是准备出发了。“他在那里!
”我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的王超。他比初中时高了很多,也更瘦了,但那副黑框眼镜没有变。
我把车随便往路边一停,拉开车门就往里冲。“王超!!”我用尽全力大喊。
人群中的王超似乎听到了,他回过头,疑惑地朝我这边看来。就在他回头的那一瞬间,
一辆失控的洒水车,像一头发狂的钢铁巨兽,毫无征兆地从公园的小路上冲了出来,
直直地撞向湖边的人群。尖叫声,碰撞声,水花四溅的声音,瞬间响彻了整个公园。
我眼睁睁地看着王超被卷入车底,那辆他心爱的山地车,瞬间被碾成了麻花。鲜血,
染红了洒水车喷出的清水,在地上蜿蜒开来。我晚了一步。我又晚了一步。
4警笛声由远及近,刺耳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我站在原地,浑身冰冷,
像一尊没有灵魂的雕塑。眼前是混乱的人群,是痛苦的呻吟,是那一片刺眼的血红。
王超的身体被卡在车轮下,已经不成形状。孙萌在我身后,死死地捂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
警察很快拉起了警戒线,开始疏散人群,勘查现场。我和孙萌作为目击者,
被带到一旁做笔录。“你认识死者?”一个看起来很老练的中年警察看着我,眼神锐利。
他胸口的警牌上写着:刘队。“……是我的初中同学。”我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
“你刚才在叫他?”刘队追问。“我……”我该怎么说?我说我预知了他的死亡?
我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一箱该死的纸鹤?“我们……我们很久没见了,今天碰巧在这里看到他,
想打个招呼。”孙萌抢在我前面,替我回答了。她的脸色苍白,但眼神却很坚定。
刘队审视地看了我们几眼,没再多问,只是例行公事地记录着。“司机说是刹车失灵了,
我们会做进一步的鉴定。”另一个年轻警察走过来说道。又是刹车失灵。又是意外。
周浩是意外触电,李琴是意外火灾,王超是意外车祸。一切都那么“合理”,
合理得让人不寒而栗。做完笔录,我和孙萌失魂落魄地回到了车上。“陈戈,
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孙萌的声音无比凝重,“这个人,或者说这个‘东西’,
它在杀人。它在利用我们身边的一切,制造‘意外’。下一个……下一个会是谁?
”下一个……我的心脏猛地抽搐了一下。周浩,施暴者。李琴,旁观者。王超,受害者。
这个名单,毫无逻辑,充满了混沌的恶意。它似乎在对当年那件事进行无差别的清算。
所有相关的人,都得死。那么,我也是相关者。我是那个躲在厕所隔间里,瑟瑟发抖的懦夫。
我是不是下一个?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再也压不下去了。我猛地发动汽车,掉头,
朝着家的方向狂奔。“你去哪?”“回家!我要看看!下一个名字是不是我!
”我的声音因为恐惧而变了调。冲进家门,
工作间里那堆五颜六色的纸鹤依旧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群沉默的秃鹫,
在等待着分食下一具尸体。我扑了过去,双手因为颤抖,几乎拿不稳任何东西。
我一只又一只地拿起它们,凑到耳边。
“嗡嗡嗡——”无数恶意的低语在我耳边汇聚成一片噪音的风暴。我的太阳穴突突直跳,
几乎要炸开。没有,没有,还是没有。就在我快要放弃,精神即将崩溃的时候,
在一只黑得像墨一样的纸鹤里,我听到了。那是一个我无比熟悉,却又让我如坠冰窟的名字。
“孙萌……”我手里的黑色纸鹤,飘然落地。我缓缓地回过头,看着站在门口,
一脸担忧地看着我的孙萌。她的脸上还挂着泪痕,眼神里充满了对我的关切和对未知的恐惧。
为什么?为什么是她?她跟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初中时,她根本就不在我们学校!
她是我上大学后才认识的!“不……不应该是你……”我喃喃自语,一步步向她走去。
“陈戈,你怎么了?你听到了什么?”孙萌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为什么是你?
”我抓住她的肩膀,几乎失去了理智,“你跟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会是你!
”孙萌被我摇晃得站立不稳,眼神里充满了迷茫和惊恐:“什么事?陈戈,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看着她惊恐的脸,一个更可怕的念头,像毒蛇一样钻进了我的脑海。这个诅咒,
它不是在清算过去。它是在折磨我。它杀掉周浩、李琴、王超,是在向我展示它的力量,
是在一步步摧毁我的心理防线。而现在,它要对我最珍贵的东西下手了。它要杀了孙萌。
它要让我亲眼看着我最爱的人,死在一场精心设计的“意外”里,而我无能为力。
这才是最残忍的报复。5“不行!我绝不允许!”我嘶吼着,将孙萌紧紧地抱在怀里,
仿佛这样就能把她和那个恶毒的诅咒隔离开。我的身体在剧烈地颤抖,一半是恐惧,
一半是前所未有的愤怒。那个藏在暗处的魔鬼,它已经不满足于重演过去的悲剧,
它要亲手导演一出新的、更让我痛苦万分的惨剧。“陈戈,到底怎么了?你听到了我的名字,
对不对?”孙萌在我怀里,声音虽然颤抖,但却异常清晰。我没有回答,只是把她抱得更紧。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她从我怀里挣脱出来,直视着我的眼睛,“从现在开始,
我们二十四小时待在一起,哪儿也不去。我不出门,不碰电,不碰火,
我不给它任何制造‘意外’的机会!”这是唯一的办法,也是最笨的办法。把自己囚禁起来,
变成一座孤岛。“对,我们哪儿也不去。”我重重地点头,拉着她走进卧室,反锁了房门。
我们拔掉了房间里所有的电器插头,关掉了手机,拉上了窗帘。整个世界,
仿佛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和窗外那个虎视眈眈的死神。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房间里一片死寂,我甚至能听到自己心脏狂跳的声音,
和孙萌紧张的呼吸声。我不敢睡,也不敢让她睡。我怕一闭上眼,再睁开时,
身边的人就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我们就这样互相依靠着,从白天坐到黑夜,
又从黑夜坐到黎明。当第一缕晨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时,我们都还活着。
“我们……我们成功了?”孙萌的声音带着一丝劫后余生的不敢置信。我也松了一口气。
也许,只要我们足够小心,就能耗死那个诅咒?然而,我太天真了。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了“咚咚咚”的敲门声。我和孙萌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惊恐。“谁?
”我压低声音问。“陈戈!开门!我是刘队!”门外传来了那个中年警察沉稳的声音。刘队?
他怎么会来?“陈戈,你再不开门,我们就要破门了!”刘队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打开了房门。门口站着刘队和两个年轻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