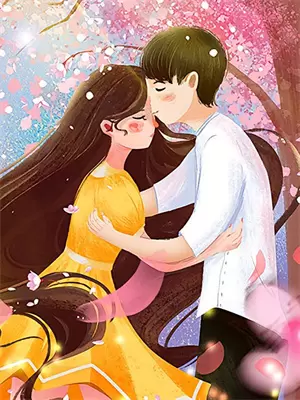初夏的风裹挟着栀子花的甜香,溜进窗棂时,正撞见方朵朵趴在书桌前,
对着电脑屏幕上闪烁的光标发愁。
文档顶端的标题“毕业创作:城市角落的微光”已经安静躺了半个月,
底下的字数却始终停留在三位数。“又卡壳了?”温润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方朵朵抬头,
看见方一凡倚在门框上,身上还带着画室里松节油的味道。他刚过而立之年,
眉眼间褪去了少年时的跳脱,多了几分沉稳,唯有笑起来时眼角的弧度,
还能让人想起那个在篮球场上挥洒汗水的少年。“哥,”方朵朵把脸埋进臂弯,闷闷地说,
“我写不出来了。感觉自己像个骗子,明明对这座城市的肌理一知半解,
却要装作洞察一切的样子。”方一凡走进来,拿起桌上的笔记本翻看。妹妹的字迹清秀,
偶尔夹杂着几处潦草的修改,字里行间能看出她对文字的虔诚。他想起十八年前,
母亲抱着襁褓里的朵朵,小心翼翼地放在他腿上时,他紧张得不敢呼吸的样子。
那时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小不点会在二十年后,成为一个为文字烦恼的文学系毕业生。
“我上次去郊区采风,看到一个老木匠,”方一凡合上笔记本,轻声说,
“他守着间不足十平米的铺子,刨子用了三十年,木头上的包浆比他额头的皱纹还深。
我问他为什么不换个新的,他说老伙计懂他的力道。”方朵朵抬起头,
眼里有了些光亮:“然后呢?”“然后我画了他三天,”方一凡笑了,“第一天他总躲镜头,
第二天会递我瓶凉白开,第三天收工时,他摸着我的画板说,这刨子的纹路,
你画得比我清楚。”他顿了顿,看向妹妹,“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在虚构,
其实是没找到那个愿意让你走进他世界的人。”方朵朵望着哥哥,忽然想起去年冬天,
她熬夜改稿时,方一凡总会端来一杯热牛奶,然后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画册,
客厅的灯一直亮到她关掉电脑。那时他刚结束一个重要的画展,正是需要休息的时候,
却默默陪着她这个“麻烦”的妹妹。“哥,你那时候准备画展,是不是也这么难?”她问。
方一凡想起三年前的夏天。画室的空调坏了,他顶着四十度的高温修改参展作品,
颜料混合着汗水滴在画布上,晕开难看的色块。经纪人打了七八个电话催稿,
他对着画布上扭曲的线条,第一次有了放弃的念头。那天晚上,他给家里打电话,
是朵朵接的,小姑娘在电话那头兴奋地说,她的散文在校刊上发表了,还念了一段给他听。
“难的时候,就想想为什么开始。”方一凡揉了揉妹妹的头发,
“你第一次把写满字的作业本拿给我看时,眼睛亮得像星星。”方朵朵的脸颊微微发烫。
她记得那是小学三年级,她写了篇关于“哥哥的画”的作文,被老师当成范文朗读。
放学回家,她举着作文本跑到方一凡的房间,他正对着一幅未完成的油画发愁,看了作文后,
却笑着把她抱起来,说:“我们家要出个小作家了。”第二天一早,
方朵朵背着帆布包出了门。她没有去图书馆,而是坐上了去郊区的公交车。车窗外,
高楼渐渐被低矮的房屋取代,她想起方一凡说的老木匠,心里忽然有了方向。半个月后,
方朵朵的毕业创作终于完成了。她写了七个城市角落里的普通人:凌晨四点扫街的环卫工,
在老巷子里修鞋的大爷,地铁口弹吉他的年轻人……文字朴实,却带着温度。指导老师看后,
在评语里写道:“你让读者看到了尘埃里的光。”她把文章发给方一凡时,
他正在外地参加艺术交流活动。深夜,手机震动,
是方一凡发来的消息:“我在酒店的落地窗前读你的文章,楼下的路灯亮得像你写的那些人,
温暖又有力量。”方朵朵看着消息,眼眶有些湿润。她想起小时候,
方一凡总会把她写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收在一个铁盒子里,说要等她出书了,就拿出来当纪念。
那时他刚考上美术学院,正为学费和颜料钱发愁,却依然把她的文字视若珍宝。
夏天快结束时,方一凡的个人画展在美术馆开幕。方朵朵特意提前到了现场,
看着工作人员把哥哥的画作一一挂起。那些画里,有雪山的巍峨,有深海的静谧,
也有城市的喧嚣,每一幅都充满了生命力。“紧张吗?
”方朵朵走到正在检查标签的方一凡身边。方一凡笑了笑:“比第一次上台演讲还紧张。
”他指向角落里的一幅画,画的是个小女孩坐在书桌前写字,窗外的月光洒在她身上,
“这幅是给你的。”方朵朵愣住了。画框里的场景,分明是她高中时的房间。
她想起有一次深夜,她伏案写作,回头时看见方一凡站在门口,手里拿着画板,
正对着她的背影勾勒。那时她还抱怨他打扰自己,现在才知道,他把那个瞬间,变成了永恒。
画展很成功。开幕式上,有记者问方一凡:“您的作品里总有一种温暖的力量,
是受到了什么影响吗?”方一凡看向台下的妹妹,她正举着相机给他拍照,
眼睛亮得像当年那个举着作文本的小姑娘。他笑了笑,声音清晰而坚定:“是家人。
他们让我知道,无论走多远,身后总有光。”活动结束后,兄妹俩走在美术馆外的林荫道上。
晚风轻拂,带着桂花的香气。“哥,下个月我的文章要在杂志上发表了。”方朵朵忽然说。
“恭喜啊,小作家。”方一凡停下脚步,认真地看着她,“我订一百本,送朋友。
”方朵朵笑着捶了他一下:“哪用那么多。”“必须的,”方一凡语气笃定,
“我妹妹的文字,值得被更多人看见。”月光穿过树叶的缝隙,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方朵朵看着哥哥的侧脸,忽然明白,所谓梦想,从来不是孤军奋战。
它是方一凡在画室里为她留的那盏灯,是她在深夜里为哥哥泡的那杯茶,
是他们在各自的轨道上奔跑时,始终望向彼此的目光。就像此刻,风里有桂花香,
身边有最亲的人,前方有各自的远方,脚下有共同走过的路。
这大概就是青春最好的模样——我们都在成为更好的自己,也在成为彼此的光。
方朵朵掏出手机,拍下哥哥的背影,配文:“我的哥哥,是画家,也是我的灯塔。
”按下发送键时,她仿佛听见,梦想的琴弦在夜色里,奏响了最动听的乐章。秋意渐浓时,
方朵朵收到了杂志社寄来的样刊。她的文章被放在了“城市剪影”栏目里,
旁边配着一张老巷弄的照片,和她文字里的意境格外契合。她摩挲着光滑的纸页,
指尖触到自己的名字时,心跳还是忍不住快了半拍。“妈肯定要把这本杂志裱起来。
”方朵朵对着电话那头的方一凡说,语气里带着抑制不住的雀跃。“何止,
”方一凡的声音里含着笑意,“上次我回家,妈还翻出你小学的作文本给邻居阿姨看,
说她女儿从小就会写东西。”方朵朵的脸颊发烫:“妈就是这样,总爱夸大其词。
”“这叫骄傲。”方一凡顿了顿,“对了,下周末我回趟家,带你去见个朋友。
她是出版社的编辑,说想聊聊你的文章。”方朵朵心里一动,
握着杂志的手指紧了紧:“会不会太突然了?我还没准备好……”“有什么好准备的?
”方一凡的声音温和却有力量,“你的文字里有别人没有的东西,那是最珍贵的。
就像我画画,技巧可以练,但对生活的感知力,是装不出来的。”挂了电话,
方朵朵走到书架前,抽出最上层的一个铁盒子。那是方一凡送给她的,
大的“作品”:歪歪扭扭的儿歌、被老师圈满红圈的作文、发表在校刊上的短文……最底下,
压着一张泛黄的素描,画的是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正趴在地上写作业,
旁边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我妹妹,未来的大作家。”那是方一凡十七岁时画的。
那时他刚学素描,笔触生涩,却把她的认真劲儿画得淋漓尽致。周末,方一凡果然回了家。
饭桌上,母亲不停给兄妹俩夹菜,嘴里念叨着:“朵朵现在出息了,
文章能上杂志了;一凡也厉害,画展办得那么成功。妈这心里啊,比吃了蜜还甜。
”父亲笑着点头:“都是他们自己努力,咱们就做好后勤。”饭后,
方一凡带着方朵朵去了一家安静的咖啡馆。出版社的编辑姓李,是个气质温婉的中年女人,
说话慢条斯理:“方小姐的文章我仔细读了,很有生活气息。现在很多年轻人写东西,
总想着往天上飘,你却愿意沉下来,看那些被忽略的人和事,这很难得。
”方朵朵有些不好意思:“我就是觉得,他们的故事值得被记住。”“这就够了。
”李编辑递过一份选题策划,“我们想做一套‘城市里的平凡英雄’系列丛书,如果你愿意,
我们可以合作。”方朵朵看着策划书上的文字,心脏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又酸又软。
她想起那些在老巷子里采访的日子:修鞋大爷给她讲他年轻时走南闯北的故事,
环卫工阿姨教她认不同的树叶,
弹吉他的年轻人把他写的歌弹给她听……原来那些被她小心翼翼收藏在笔记本里的瞬间,
真的可以变成一本书。“我愿意。”她抬起头,眼里闪着光。从咖啡馆出来,秋阳正好,
透过梧桐叶洒在地上,像铺了一层碎金。“我就知道你可以。”方一凡递给她一杯热可可。
“哥,”方朵朵吸了口热饮,暖意从喉咙一直淌到心里,“要是我写砸了怎么办?
”“那就再写。”方一凡说得轻描淡写,“我第一次办画展,有人说我的画像小孩子涂鸦,
我难受了好几天,后来不还是拿起画笔了?创作这回事,不怕犯错,就怕不敢试。
”他顿了顿,看着妹妹:“再说了,你背后有我呢。写不下去了,
哥带你去采风;被编辑退稿了,哥请你吃大餐;要是想放弃了……”“我才不会放弃。
”方朵朵打断他,语气坚定,“就像你从来没放弃过画画一样。”方一凡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