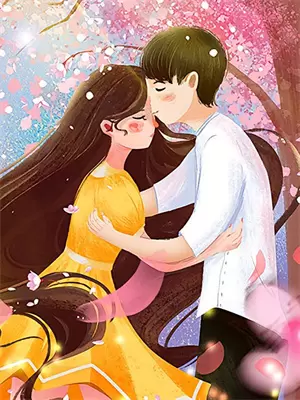林晚第一次见到陈砚时,是梅雨季的第七天。雨已经缠缠绵绵下了整整一周,
像被谁失手扯断的银线,密密麻麻织在老街的上空,把青石板路浸得发亮,
倒映着两侧斑驳的砖墙和垂落的雨帘。雨丝落在青瓦上是“沙沙”的轻响,
打在巷口老榕树的阔叶子上是“簌簌”的摩挲,滴进墙角的积水洼里,
又溅起“叮咚”的脆声——三种声音混在一起,成了老街独有的梅雨季背景音,
裹着潮湿的草木气息,漫在空气里。
林晚怀里抱着一摞刚从城西“老周染坊”收回来的棉麻布料,
最上面那匹靛蓝扎染布是她的心头宝。这块布是她跟着外婆学染布时,亲手染的第一块成品,
布面上的缠枝纹是她花了三个晚上,
用细如发丝的银线一针针绣上去的——银线在靛蓝色的布面上泛着淡淡的光,
像藏在夜色里的星星。客户是个要办中式婚礼的姑娘,下周就要取货,
说要用来做婚服的衬里,“要带着手作温度的布,才配得上一辈子的日子”。
她要去的“晚巷手作”,是外婆留下的小店。店面不大,木门上挂着块梨木招牌,
“晚巷手作”四个字是外婆五十岁那年写的,笔锋软乎乎的,却透着股执拗的认真。
招牌的木纹里藏着不少岁月痕迹:右上角有几处细小的裂纹,
是去年台风天被风吹裂的;中间还有一块浅褐色的印子,是林晚刚接手时,
不小心把墨汁洒上去的——当时她蹲在门口哭了半天,觉得把外婆的东西弄坏了,
后来还是巷口的张阿姨安慰她,“墨渍也是缘分,跟这块招牌融在一起,就成新故事了”。
从那以后,林晚每天开店前都会摸一摸那块招牌,指尖蹭过木纹和墨渍,
像在和外婆悄悄打个招呼。这天路过巷口老榕树时,脚下突然一滑。后来她才知道,
是隔壁“阿福面馆”的伙计小王,早上打扫时泼了盆肥皂水在台阶上,
赶时间送外卖没来得及冲干净,被雨水泡了大半天,滑得像涂了层猪油。
身体不受控往前扑的瞬间,林晚脑子里第一个念头不是自己会不会摔疼,
而是怀里的扎染布——她下意识地把布料往怀里紧了紧,可惯性还是让布料散了一地,
最宝贝的那匹扎染布被风卷着,飘进了台阶下的积水里,银线绣的缠枝纹浸在水里,
像要被冲散似的。“小心!”一只温热的手突然扣住她的手腕,力道不大,却稳得像锚。
那只手的掌心带着点薄茧,指腹蹭过她手腕内侧细腻的皮肤时,有点磨砂的质感,却不硌人,
反而让她慌乱的心跳瞬间稳了半拍。林晚被拉回台阶上时,呼吸都有些发颤,
抬头撞进一双沉静的眼睛里——男人的眼睛是深棕色的,像浸在温水里的琥珀,
没有一点急躁,反而透着股平和,连眉峰都是舒展的,不像平时遇到的路人,
总带着梅雨季的烦躁。他穿件浅灰色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腕骨上一道浅淡的疤痕。
疤痕大概两指宽,边缘很平整,不像是意外划伤,
倒像是什么时候被工具轻轻蹭到的——后来林晚才知道,
那是他十八岁第一次独立做建筑模型时,被美工刀划到的,当时流了不少血,
他却舍不得去医院,找了块创可贴随便贴了贴,结果留了个浅印子。
他总说这疤痕是“入门礼”,提醒自己做设计要心细,不能急。男人没等她道谢,
就弯腰去捡水里的扎染布。他的动作很慢,指尖捏着布角时,
特意避开了上面的缠枝纹——仿佛隔着布料都能察觉到银线的金贵,
连拧水都顺着布纹的方向,指腹轻轻挤压,没让水流把绣线冲得打结。
他又把散落的其他布料一一叠好,每一块都叠得方方正正,连布角被风吹得翘起的褶皱,
都用指腹慢慢压平,动作轻得像在呵护一件易碎的瓷器,生怕弄坏了半分。“这块布要阴干,
不能晒。”他把叠好的布料递过来,声音像雨打在青瓦上,清润又平和,
没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客气。他的目光落在林晚发红的脚踝上,眉头轻轻蹙了一下,
蹲下身看了看:“崴到了吗?脚踝都肿了。前面有家‘张记糖水铺’,我去买杯姜撞奶,
你暖暖脚?姜撞奶要热的才管用,凉了驱寒的效果就差了。
”林晚的脸颊比刚出锅的姜撞奶还烫,连耳根都热得发疼。她连忙摇头,把布料抱得更紧,
布料的潮气蹭在下巴上,却没觉得凉:“不用不用,谢谢您,我自己能走。您看,
我脚踝就是有点红,不疼的。”接过布料时,她的指尖不小心蹭到他的手背,
那片薄茧又触到了——这次她看清了,茧子主要在指腹和指节处,
是常年握笔、敲键盘和摆弄建筑模型留下的,像给手指裹了层薄薄的磨砂纸,
带着常年和工具打交道的踏实感。男人笑了笑,没再坚持。他抬眼往林晚身后望了望,
目光落在“晚巷手作”的招牌上,又指了指右边的钉子:“风把招牌吹斜了,
右边的钉子松了,再刮大点风,说不定会掉下来砸到人。我车里有工具,帮你修修?
反正我今天的调研也不急,早做完晚做完都一样。”那天下午,
陈砚从他停在巷口的银灰色轿车里,翻出了一个深棕色的帆布工具包。
工具包的边角磨得有些发白,
拉链上挂着个小小的铜制钥匙扣——是个迷你的哥特式教堂模型,
窗户上的花纹、门上的浮雕都做得精致,一看就是亲手做的。他说这是大学毕业时,
爷爷送他的礼物,爷爷是个老木匠,一辈子和木头打交道,“爷爷说,做设计和做木活一样,
都要用心,不能糊弄”。他拿出螺丝刀、扳手,还有一小盒不同型号的钉子,
蹲在店门口的台阶上,仰头看着招牌。雨还没停,细细的雨丝落在他的头发上,
沾了层薄雾似的水珠,他却没在意,只是从口袋里掏出块叠得整齐的格子纸巾,
仔细擦了擦螺丝刀上的灰,才开始动手。林晚在店里煮了茶。茶是外婆留下的老白茶,
装在一个粗陶罐里,罐身上有外婆手绘的小兰花,花瓣边缘有点模糊,
是常年摩挲留下的痕迹。她抓了一小撮茶叶放进盖碗,用刚烧开的沸水冲泡,
茶叶在水里慢慢舒展开,飘出淡淡的药香和枣香——外婆以前总说“急不得,
好茶得等三分钟,滋味才出得来”。林晚端了杯茶走出去,
递到陈砚手边:“先喝点茶暖暖吧,不急的,反正今天也没什么客人。”陈砚接过茶杯时,
指尖碰到杯壁,轻轻顿了一下,像是怕自己手凉,把杯子捂热了才递回来一点:“谢谢。
”他喝了一口,眼睛亮了亮,抬头看向林晚:“这茶有回甘,
和老街的味道很像——我之前在别的地方喝的老白茶,要么太淡,要么太涩,都没这么醇。
”林晚没接话,只是站在屋檐下,看着他修招牌的背影。他蹲在那里,脊背挺得很直,
手里的螺丝刀转得很稳,每拧一下都会低头看一眼,确认钉子是否牢固,
偶尔还会用扳手轻轻敲两下,调整角度。雨水滴进他的衣领,他也只是抬手抹一下,
指尖蹭过锁骨时,动作很轻,像怕碰疼自己似的。修完招牌时,雨已经小了很多,
天边透出点淡淡的光,像蒙在玻璃上的雾被擦开了一角。陈砚把工具收进包里,
又仰头检查了一遍,还用手推了推招牌,确认稳固了才放心:“应该没问题了,
右边的钉子我换了个粗点的,防锈的,下次再刮风也不会歪了。”他喝了半杯茶,
就准备走了——临走前才想起自我介绍,手还抓着工具包的拉链,
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叫陈砚,是隔壁街区‘筑境’建筑事务所的设计师,
最近在做老巷改造的调研,经常会来这边转一转,收集点老建筑的资料,
比如墙上的砖纹、门口的石墩,这些都是老巷的记忆,不能丢。”林晚站在门口,
看着他撑着一把黑色的伞,走进雨雾里。浅灰色衬衫的衣角被风吹起,像一片轻盈的云,
渐渐消失在巷口的拐角处。她低头看了看手里的茶杯,
杯沿上还留着他的唇印——小小的一圈,带着点茶渍的淡褐色,像给杯子盖了个温柔的戳。
心里忽然泛起一阵细碎的痒,像有小虫子在爬,连空气里的雨味都变得甜了些。她回到店里,
把那杯没喝完的茶又热了一遍,喝的时候,总觉得比平时多了点回甘,连舌尖都带着暖意。
之后的日子,他们总能在老街偶遇,像是有什么无形的线,把两人的轨迹缠在了一起。
有时是早上七点多,林晚在巷口的“李记早餐铺”买豆浆油条。
早餐铺的张阿姨是看着林晚长大的,每次都会多给她加一勺自己腌的咸菜:“小林,
今天也这么早开店啊?你外婆以前也总这个点来,说早上的豆浆最鲜,
油条要刚炸出来的才脆。”林晚刚接过装着豆浆的塑料袋,指尖还沾着袋子的温热,
就看见陈砚从对面的巷口走过来。他手里拿着个棕色的牛皮笔记本,
封面上用钢笔描了老巷的速写——是巷口的老榕树,枝叶画得很细,
连垂下来的根须都一根一根画了出来,旁边还标着“树龄约80年,枝繁叶茂,可遮荫”。
他见到林晚时,脚步顿了顿,把伞往她这边倾了倾,自己半边肩膀露在雨里:“早,
今天的雨好像比昨天小了点,风也软了。”两人就站在早餐铺的屋檐下,聊上几句。
陈砚会说他早上调研时看到的趣事,比如巷尾第三家的院墙上,爬满了三角梅,
虽然是梅雨季,却开得特别艳,花瓣上还沾着水珠,
像撒了把碎钻;林晚会说她今天要做的手作,比如给客户定制的银质书签,
要刻上“读书不觉已春深”的句子,现在还在想刻什么字体——隶书太庄重,楷书太规整,
行书又怕客户觉得不秀气。陈砚听了,从笔记本里翻出一张纸,给她画了几种字体的小样,
“你看,把行书的笔画写得柔一点,再在‘春’字旁边加片小叶子,
会不会更符合手作的感觉?”林晚看着纸上的字,笔尖的弧度刚好,小叶子也画得可爱,
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软乎乎的。有时是中午十二点,
林晚在巷口的“王记裁缝店”取纽扣。裁缝店的王阿姨是个话多的老太太,总爱跟她聊家常,
手里缝着衣服,嘴里也不停:“小林啊,你上次说的那个小伙子,就是帮你修招牌的那个,
我昨天还看见他在巷口的老墙前蹲了半天,拿着尺子量来量去,还摸那些砖,
一看就是个认真的孩子——现在这么踏实的年轻人不多了。
”林晚刚拿到装着珍珠纽扣的小盒子,盒子是王阿姨用碎花布缝的,摸起来软乎乎的,
就看见陈砚蹲在不远处的老墙前,手里拿着卷尺,正在记录砖纹。那面老墙是民国时期的,
砖面上有很多细小的纹路,还有些模糊的刻字——据说是以前住在这里的学生刻的,
有“读书救国”,还有“民国二十五年夏”。陈砚蹲在那里,很专注,
连林晚走到身边都没发现。他的笔记本摊在膝盖上,上面画着砖墙的剖面图,
还标了砖的尺寸、颜色,甚至连砖缝里长的小草都画了下来。“这墙有什么特别的吗?
”林晚轻声问,怕打扰到他。他抬头,眼里还带着点刚从图纸里拔出来的专注,看到是她,
才笑了笑:“这墙的砖是‘清水砖’,民国时期很常见,不用抹灰,直接露着砖面,
现在很少见了——你看这块砖,”他指着一块颜色稍深的砖,“上面还有当时工匠的手印,
应该是烧砖时不小心按上去的,留了这么多年,也算个小纪念。老建筑就像老人,
这些细节都是它的故事,我得记下来,改造的时候才能保留住。”林晚凑过去看,
那块砖上果然有个淡淡的手印,指节的痕迹还能看清,心里忽然觉得,
陈砚看这些老建筑的眼神,和自己看老物件的眼神很像——都带着点敬畏,又带着点温柔。
有时是下午三点,林晚在“张记糖水铺”买绿豆沙。糖水铺的张叔记得她的口味,
每次都会少放糖,还会多给她加一勺薏米:“小林喜欢清淡点的,对吧?
你外婆以前也爱喝我家的绿豆沙,说解腻,夏天喝了不中暑。”林晚刚坐下,
把包放在旁边的椅子上,就看见陈砚推门进来。他身上还带着点雨气,头发梢上沾着水珠,
进门时还下意识地抖了抖伞上的水,怕弄湿地面。他走到柜台前,对张叔说:“一碗双皮奶,
不加红豆,多放两勺奶。”张叔笑着打趣:“今天怎么不加红豆了?平时不都要双份红豆吗?
嫌不够甜?”陈砚的目光往林晚这边扫了一眼,耳朵有点红,小声说:“今天想尝尝原味的,
看看和加红豆的有什么不一样。”林晚低头搅着绿豆沙,勺子碰到碗壁,
发出“叮当”的轻响,心里却像被糖水浸过,甜丝丝的。陈砚在她对面坐下,
拿出手机里的设计图,把屏幕调亮了点,递到她面前:“这是我做的老巷改造初步方案,
你看这里,”他指着巷口的位置,“我想把巷口的老榕树周围修个小平台,用老石板铺地面,
再放几张石凳,石凳的造型我想做成木榫的样子,和老巷的风格搭。
这样大家累了可以坐下来歇脚,你看店累了,也能出来坐会儿。”林晚凑过去看,
设计图上的老榕树画得很像,连枝叶的走向都和现实里的差不多,小平台的尺寸也刚好,
不会挡住行人。“挺好的,”她小声说,“这样街坊邻居就有地方坐了,
夏天还能在树下乘凉。”陈砚听了,眼睛亮了亮,
又翻出几张细节图:“我还想在平台旁边种点薄荷,夏天能驱蚊,你要是喜欢,
还能摘点泡水喝——你上次说喜欢薄荷味的东西,对吧?”林晚愣了一下,
才想起自己上次在早餐铺随口提过一句,没想到他记下来了,心里像揣了颗糖,
连绿豆沙都觉得更甜了。陈砚话不多,却很会听。林晚总爱跟他说做手作时的趣事,
他每次都听得很认真,眼睛看着她,像在看一件很珍贵的东西,偶尔还会提出些小建议,
都说到她心坎里。
她会说给客户做结婚对戒时的波折:“那对戒指是给一对结婚十年的夫妻做的,
他们想在戒指内侧刻上‘十年’和彼此的生日。我第一次融银料时,温度不够,银料没融透,
倒出来的戒指有气泡;第二次不小心加了太多焊药,戒指颜色发暗,
不像纯银;第三次我守在熔炉旁,盯着温度表,每隔一分钟就看一次,终于成功了。
客户拿到戒指时,女的哭了,说‘这戒指带着你的温度,比买的贵的还好看’,
我当时也差点哭了。”陈砚听了,点了点头:“手作的意义就是这样,有温度,有故事。
就像我做设计,每次看到老建筑在自己手里变好看,还能保留住原来的味道,就觉得特别值。
”他还会问细节:“融银料的温度要控制在多少啊?是不是很难把握?”林晚就跟他讲,
纯银的熔点是961.78℃,要刚好达到这个温度,不能高也不能低,“就像煮茶,
差一点都不行”。她还会说修复外婆留下的旧手帕时的意外:“那块手帕是外婆年轻时用的,
边角破了个洞,上面还有她绣的小梅花。我想把破洞补好,就拆了梅花周围的线,
结果在夹层里发现了半张民国时期的车票——是从上海到苏州的,日期是1948年的秋天,
车票上还有外婆的名字,用钢笔写的,字和她后来写的很像。我问了张阿姨,
她说外婆年轻的时候去过上海,是去看她的姐姐,没想到还留着车票。
”陈砚接过手帕看了看,手帕的布料已经很薄了,颜色也有点发黄,却很干净,
梅花的绣线还很亮。“这车票是很珍贵的纪念,”他小心地摸了摸车票,
“你可以找个小相框装起来,放在店里,既是外婆的回忆,也是手作店的故事。
”林晚觉得这个主意好,后来真的找了个原木相框,把车票和手帕的一角装起来,
挂在收银台后面,客人看到了,都会问起这个故事,店里的气氛也变得更暖了。
林晚渐渐发现,自己的生活里,到处都有了陈砚的影子。
她会下意识地在下午三点望向窗外——因为陈砚总在这个时候来老街调研,
有时会从店门口经过,往里面看一眼,看到她在忙,就会对着她笑一笑,
然后继续往前走;她会在煮茶时多放一勺茶叶,因为陈砚说过老白茶要浓一点才回甘,
她想下次他来的时候,能喝到合口味的茶,还会提前把杯子温好,
怕茶水凉得快;她会在设计新的手作时,不自觉地加入他喜欢的元素——比如做木盒时,
在盒盖刻上他提过的“青瓦纹”,青瓦的弧度要和老巷的瓦一样;做银镯子时,
在镯身刻上简单的“榫卯结构”,榫头和卯眼要刚好合上,想着他看到会喜欢。
她不是没谈过恋爱。大学时谈过一个男朋友,会说很多甜言蜜语,
比如“你是我见过最可爱的女生”,却记不住她不吃香菜,
每次点外卖都要她自己挑半天;工作后认识过一个男生,会送很贵的礼物,
比如名牌口红、香水,却从来没问过她做手作时累不累,甚至觉得她做手作“赚不了几个钱,
不如找个稳定的工作”。只有陈砚,他不会说好听的话,却会在她搬布料时,
默默走过来搭把手,把重的布料都自己扛着,还会说“你别搬,这些布料沉,我来就好,
你要是累着了,手作就做不了了”;会在她熬夜赶订单时,发来“记得喝热粥”的消息,
有时还会附上一张自己煮的粥的照片——白粥里放了点红枣和桂圆,看起来很暖,
还会提醒她“别熬太晚,凌晨一点前一定要睡觉,
不然对眼睛不好”;会在她抱怨老街停电时,提着应急灯出现在店门口,
应急灯是他从车里拿的,还带了两根蜡烛和一个打火机,说“万一应急灯没电了,
还能用蜡烛,你做手作要看清楚,不能伤到手”。七月初,梅雨季结束的那天,天空放晴了。
阳光透过云层,洒在老街上,把青石板照得发亮,连空气里的潮气都散了不少,
带着点草木的清香。陈砚约林晚去“张记糖水铺”吃双皮奶,说是“庆祝梅雨季结束,
也庆祝老巷调研完成了一部分”。店里的风扇转得慢悠悠,扇叶上积了点灰,
转起来带起的风都带着点旧时光的味道,吹在脸上凉丝丝的,刚好压下七月初的暑气。
张叔端来两碗双皮奶,林晚的那碗上放了点红豆,颗颗饱满,
陈砚的那碗没有——他把自己碗里仅有的几颗红豆,也都拨到了林晚碗里,
指尖碰到她的碗沿时,轻轻顿了一下:“我不爱吃甜的,你吃吧,红豆多吃点好,补血。
”林晚搅着碗里的红豆,红豆的甜混着双皮奶的香,在嘴里化开,心里像被糖水浸过,
甜丝丝的。这时,陈砚忽然开口了,声音比平时低了点,带着点认真,
手指还在碗沿上轻轻划着圈:“下周末我要去邻市出差,那边有个‘青溪古村落’修复项目,
是个很老的村子,里面有很多老木作手艺——有个做了五十年木榫的老匠人,姓王,
他做的榫卯不用一根钉子,能撑几十年不变形,连故宫的修复师傅都夸过他。
我想拍点照片回来给你看,还有老匠人做木活的细节,比如怎么选木头、怎么凿榫卯,
说不定对你做手作有帮助。”林晚的心跳漏了一拍,手里的勺子停在半空。她抬头看陈砚,
他的眼睛里有细碎的光,像把阳光揉碎了放进去,连眉峰都带着点期待。“要去多久啊?
”她小声问,声音有点发颤,怕自己问得太急,显得不矜持。“大概十天。”陈砚看着她,
手指轻轻碰了碰碗沿,像是在鼓足勇气,“等我回来,带你去看古村落的晒秋。我查过了,
那个时候刚好是晒秋的季节,村民会把玉米、辣椒、南瓜都晒在竹匾里,从山脚排到山腰,
黄的、红的、橙的,像给山披了件花衣裳,特别好看。我还问了王匠人,他说晒秋的时候,
村里会做桂花糕,用自己种的桂花,甜而不腻,你肯定喜欢。”林晚点头,
把脸埋进双皮奶的甜香里,不敢看他的眼睛。她其实想说“我等你回来”,
想说“你要注意安全,别太累了”,还想说“我会想你的”,可话到嘴边,
却只挤出了一句“你注意安全”,声音小得像蚊子叫。陈砚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只是把自己的勺子擦干净,递给她:“你的勺子好像有点歪,用我的吧,我的勺子是圆头的,
挖双皮奶更方便。”林晚接过勺子,勺柄上还带着他的温度,暖得她指尖都发烫。
陈砚出差前的那几天,两人见面的时间多了些。他会在下班后过来,帮林晚整理布料,
把不同颜色、不同材质的布料分类叠好,还会在每摞布料上贴个小标签,
写着“适合做布偶”“适合做手帕”;林晚会帮他整理调研笔记,把散落的纸张按日期排好,
在里面夹了一张自己绣的小兰花书签,兰花的颜色是淡蓝色的,和他衬衫的颜色很像。
出发前一天,陈砚来店里拿笔记本,看到书签时,愣了一下,然后小心翼翼地拿起来,
对着光看了看:“这是你绣的?真好看。”林晚点头,有点不好意思:“就是随便绣的,
你要是不喜欢,可以拿下来。”他连忙摇头,把书签夹回笔记本里,
还特意夹在第一页:“喜欢,特别喜欢。我带着它出差,就像你在身边一样,
调研的时候都有动力了。”林晚看着他认真的样子,心里像揣了颗糖,连空气都甜了。
陈砚出差的第三天,林晚正在店里给一对银镯子刻花纹。
银镯子是给一对结婚五十年的老夫妻做的,爷爷说要刻上“相伴”两个字,
奶奶说要在字的旁边刻上小小的缠枝纹,“像我们俩,缠缠绕绕一辈子”。林晚拿着刻刀,
小心翼翼地在镯身上刻着字,刻刀划过银面,发出“沙沙”的轻响,银屑落在工作台上,
像撒了层碎银。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工作台上,把银镯子照得发亮,
连刻刀的影子都变得温柔。就在这时,手机突然响了。来电显示是个陌生号码,
归属地是邻市。林晚皱了皱眉,还是接了起来——她以为是客户打来的,
最近有几个客户要定制手作,经常会打电话确认细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急促的男声,
声音里带着点慌乱,还有点刻意的紧张:“请问是林晚小姐吗?我是陈砚的同事,我叫李涛。
陈砚他……他在去青溪古村落的路上出车祸了,现在在邻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
需要交五万块手术费!他的手机摔坏了,开不了机,口袋里只有你的联系方式,
你能不能先把钱转过来?医院说不交钱就不安排手术,情况特别紧急,再晚就来不及了!
”林晚手里的刻刀“当”地掉在工作台上,银镯子滚到了桌角,撞在装银料的盒子上,
发出“哐当”的响。她的脑子一片空白,像被谁用橡皮擦过,
只剩下“车祸”“抢救”“五万块”这几个词在耳边打转,嗡嗡作响。她抓着手机,
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指节都泛了青,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你……你说什么?
陈砚他出车祸了?在哪个医院?邻市第一人民医院吗?抢救室的编号是多少?”“对!
就是邻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抢救室!编号我没记住,太急了!”那个男声更急了,
还带着点不耐烦,“林小姐,你快点转钱吧,账号我现在发给你,你转过来后给我回个电话,
我好跟医院说安排手术!陈砚现在还在里面躺着,血压都不稳定,你别耽误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