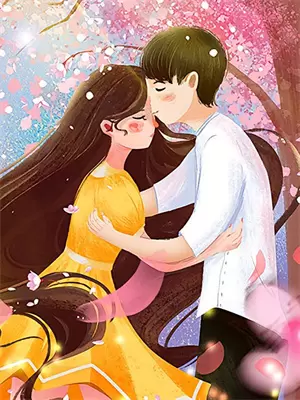贾旭在一阵撕裂般的头痛中睁开眼,入目是土坯墙和糊着旧报纸的屋顶,
空气中飘着一股淡淡的霉味和烟火气。这不是他熟悉的医院,更不是退伍后即将踏入的新家。
“嘶——”他撑着炕沿坐起身,脑子里像被塞进了一团乱麻。
无数陌生的记忆碎片涌进来:18岁的年纪,北平现在该叫北京了的红星轧钢厂,
父亲工伤去世后留下的接班名额,还有一个叫“贾东旭”的名字。他,贾旭,
一个刚退伍的兵,在救一个横穿马路的小姑娘时被酒驾的车撞飞,再睁眼,
竟成了《情满四合院》里那个活不过几集的倒霉蛋贾东旭。“呵,这叫什么事儿。
”贾旭低笑一声,揉着发胀的太阳穴。前世闲时看过这部剧,
对院里那点鸡飞狗跳的事记得清楚。贾东旭性子软,撑不起家,早早没了后,
老娘贾张氏和媳妇秦怀茹被院里那群“人精”算计得够呛。“庙小妖风大,水浅王八多。
”他咂摸了句剧里的评价,心里却没多少鄙夷。能在兵荒马乱里活下来,
还在这四合院里扎下根的,哪个不是揣着七八副心思?这年头日子紧巴,
为了一口吃的、一块布票算计,虽不体面,却也真实。只是,他贾旭不是原主。部队十几年,
练的是筋骨,磨的是性子,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还能被这点家长里短困住?
他低头看了看身上的粗布褂子,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记忆里,
原主昨天跟院里的傻柱、许大茂几个喝了顿酒,大概是想着明天就要去轧钢厂接班,
心里激动,没成想酒量不济,直接喝断了气——倒便宜了自己。“东旭!东旭!你可算醒了!
”门外传来女人的喊声,带着点急切,还有几分熟悉的粗粝。贾旭拉开门,
就见一个穿着灰布袄的中年妇人站在院里,手里还攥着块抹布,正是他这一世的娘,贾张氏。
记忆里的贾张氏,后期泼辣蛮横,是院里的“混不吝”,可眼前的她,鬓角已经有了白发,
眼角的细纹里藏着担忧,看着倒像是个寻常的母亲。“妈。”贾旭喊了一声,声音有些生涩。
贾张氏眼圈一下子红了,上来就拉着他的胳膊左看右看:“你这孩子,跟你说少喝点少喝点,
偏不听!昨天回来跟滩泥似的,吓死妈了!”她一边说,一边往屋里拽他,“快进屋,
妈给你熬了粥,放了点红糖,暖暖胃。”屋里的小桌上摆着个粗瓷碗,粥是稀的,
能照见人影,上面飘着几粒米,红糖沉在碗底,甜香却很实在。贾旭知道,
这在眼下已经算是好东西了。“昨天……跟谁喝的?”贾旭喝了口粥,红糖的甜混着米香,
熨帖了空荡荡的胃。“还能有谁,傻柱、许大茂那几个呗。”贾张氏坐在旁边纳鞋底,
嘴里絮叨着,“傻柱还行,就是直了点;许大茂那小子,油嘴滑舌的,你少跟他掺和。
”贾旭点点头,没多说。傻柱的憨厚,许大茂的奸猾,他心里有数。“对了,
”贾张氏抬头看他,眼神里带着期盼,“明天去厂里,记着跟你一大爷问好。
他在钳工组当组长,你去了正好在他手下,机灵点,多学学。”一大爷易中海,
贾旭记得这人。表面上是院里的“老好人”,实则精于算计,
一门心思找个能给他养老的“接班人”。原主性子软,怕是早就被他划进了“可培养”名单。
“知道了。”贾旭应着,心里却有了计较。易中海的手艺是真本事,学过来是自己的,
但至于当“养老工具”,那得看他乐意不乐意。吃完粥,贾旭起身收拾。
他找出原主准备好的蓝布工装,浆洗得板正,就是布料硬得硌人。他叠得方方正正放在床头,
又把屋里扫了一遍,动作利落,带着部队里的习惯。贾张氏看着儿子的背影,愣了愣。
以前的东旭,屋里乱得像狗窝,喊他收拾能磨蹭半天,今天怎么转性了?她没多问,
只是嘴角悄悄翘了翘。傍晚的时候,院里开始热闹起来。下班的、做饭的、喊孩子回家的,
声音此起彼伏。贾旭站在门口,看着院里的景象:中间是共用的水龙头,旁边堆着煤球,
各家的烟囱冒着烟,空气里混着煤烟味和饭菜香。傻柱端着个大碗从对面屋出来,
碗里是白菜炖豆腐,还飘着点油花。看见贾旭,他咧嘴一笑:“东旭,醒了?昨天没喝够啊,
今天再整两杯?”“不了,明天还要上班。”贾旭摇摇头,语气平淡。傻柱“嘿”了一声,
也不勉强,呼噜呼噜喝着汤走了。紧接着,许大茂叼着烟卷晃了过来,穿着干净的干部服,
头发梳得油亮。“哟,东旭醒了?我说你这酒量也太差了,昨天才喝了两盅就倒了。
”他语气里带着点戏谑。贾旭瞥了他一眼,没接话。许大茂讨了个没趣,讪讪地走了。
贾张氏在屋里看见了,出来拉了拉贾旭的胳膊:“跟他置气干啥,不值当。”“没置气。
”贾旭淡淡道,“就是不想跟他废话。”他心里清楚,许大茂这种人,你越搭理他,
他越上赶着来事。晚饭是窝窝头就咸菜,贾旭吃得很香。在部队的时候,
比这差的伙食都吃过。贾张氏看着他吃得实在,
把自己碗里的窝窝头掰了一半给他:“多吃点,明天上工有力气。”贾旭没接,
把自己的递过去一半:“妈,你也多吃。我年轻,饿不着。
”贾张氏看着碗里多出的半个窝窝头,眼眶又热了。这儿子,好像真的不一样了。夜深了,
院里安静下来,只有偶尔传来的咳嗽声和远处的狗吠。贾旭躺在硬邦邦的土炕上,睡不着。
他想起牺牲的战友,想起救那个小姑娘时最后看到的阳光,
想起父母在村口等他退伍回家的身影。心里不是不难受,但更多的是一种韧劲。活着,
就得好好活。不管在哪儿,不管是谁。他贾东旭,明天就要去轧钢厂上班了。
凭着在部队练出的眼力和手上的准头,凭着这一身不服输的劲,不信过不好这日子。
至于院里的那些算计,那些纷争,他没兴趣掺和,但谁要是想把主意打到他头上,
他也不是吃素的。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棂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贾旭攥了攥拳头,
骨节发出轻微的声响。明天,会是新的一天。第二章 初入轧钢厂天刚蒙蒙亮,
贾东旭就着院里的露水洗漱完毕。蓝布工装穿在身上,浆洗后的硬挺蹭着皮肤,
倒让他想起部队的作训服——都是要靠力气和规矩立身的地方。
跟着院里的工人往轧钢厂走时,晨雾还没散,远处的厂房像一头蛰伏的巨兽,
烟囱里冒出的烟慢悠悠地融进雾里。保卫处的人检查了他的接班证明,
领着他往红砖小楼走:“人事部在三楼,办完手续直接去钳工车间,有人接应。
”人事部的办公室里摆着几张木桌,文件堆得老高。一个戴眼镜的干事核对了档案,
在表格上盖了章,又喊来个穿灰色中山装的中年男人:“老王,这是贾东旭,顶他父亲的班,
分到你们钳工车间。”被称为老王的是钳工车间的主管,脸上带着常年被机油浸过的黝黑,
拍了拍贾东旭的肩膀:“老贾的儿子?跟我来。”车间里比想象中更嘈杂,
车床的轰鸣声震得耳膜发颤,空气中飘着铁屑和机油的味道。老王领着他穿过一排排机床,
指着最里面的区域:“去一工段,找张组长。”一工段的组长张师傅是个矮胖的汉子,
正叉着腰训人,见老王过来,立刻堆起笑:“王主管,这是?”“老贾的儿子,贾东旭,
今天第一天来。”老王指了指贾东旭,“给他安排个人带带,按规矩来。
”张师傅打量着贾东旭,又扫了眼工段里的人,
最后目光落在角落里一个正低头锉零件的身影上:“老易,你看?”那人闻声抬头,
正是易中海。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袖口卷到胳膊肘,露出结实的小臂,
手里的锉刀在零件上平稳地滑动,连带着肩膀都没怎么动。他看了贾东旭一眼,
又转向张师傅,声音不高不低:“行,我带吧。”张师傅松了口气,他知道易中海的本事,
别看这人不爱说话,手艺在整个车间都是顶尖的,平时别说带徒弟,就是问他个技术活,
都得看他心情。今天能应下来,多半是看在老贾的面子上。“那成,东旭,
以后就跟着易师傅学。”张师傅拍了拍贾东旭的背,“好好学,老易的手艺,
学三成就能混饭吃了。”贾东旭点点头,对着易中海鞠了一躬:“易师傅。
”易中海“嗯”了一声,没多话,指了指脚边的一堆毛坯件:“先把这些倒角磨了,
用细砂纸,磨到不扎手为止。”说完,转身继续锉他的零件,
仿佛身边多出来的人只是台不会说话的机器。贾东旭没在意。他知道这年代的手艺人都这样,
本事藏得深,不会轻易露。他拿起砂纸,按易中海说的,一点点磨零件的边角。
铁屑沾在手上,混着汗水,又痒又涩,磨到中午时,指尖已经泛了红。中午打饭的哨声一响,
工人们都往食堂涌。易中海放下锉刀,从墙角拎起两个铝饭盒,递给贾东旭一个:“一食堂,
自己打。”贾东旭接过饭盒,见饭盒上用红漆写着个“易”字,边角都磕掉了漆。
他跟着人流到了一食堂,排着队往前挪,前面的人喊着“要白菜”“要萝卜”,
窗口里的师傅就用大铁勺舀相应的菜,分量都差不多,顶多是给相熟的人多抖半勺。
轮到他时,贾东旭才发现掌勺的是傻柱。傻柱穿着白围裙,额头上全是汗,看见他愣了一下,
随即压低声音:“东旭哥?要啥?”“两份白菜,四个二和面馒头。
”贾东旭把两个饭盒递过去。傻柱手里的勺没停,给两个饭盒里都舀了白菜,
又在易中海的那个饭盒底下悄悄多压了两块肥肉,飞快地盖上盖子:“拿着,赶紧走,
后面等着呢。”贾东旭接过来,低声道了谢。他知道,这两块肉,是傻柱能给的最大体面了。
回到工段,易中海正坐在机床旁的木凳上抽烟。贾东旭把饭盒递过去,易中海打开看了眼,
没说话,拿起馒头就着白菜吃起来。他吃饭不快,每一口都嚼得很细,像在琢磨什么事。
贾东旭也跟着吃,馒头有点干,白菜没什么油星,可他吃得认真。在部队时野外拉练,
啃冻硬的窝头都觉得香,这点苦不算什么。下午,易中海让他给机床换砂纸,
又让他递扳手、拿量具,全是些没技术含量的杂活。贾东旭都干得利落,
递工具时永远是把儿朝着易中海,换下来的废砂纸也都规规矩矩堆在墙角。易中海看在眼里,
手里的活没停,心里却有数。这孩子比他想象中稳当,不像院里其他年轻人那样毛躁,
也没因为是老贾的儿子就摆谱。快收工时,贾东旭看见二大爷刘海中从锻工车间那边过来,
光着膀子,脊梁上全是汗,手里拎着的大锤看着就沉。刘海中看见他,扬了扬下巴:“东旭,
第一天上班,还行?”“挺好的,二大爷。”贾东旭笑着应道。“锻工车间才是真练本事!
”刘海中拍着胸脯,“你看我这胳膊,抡十年锤练出来的!”正说着,锻工车间的组长喊他,
他应了一声,又对贾东旭说,“有空去我那儿坐坐!”说完,大步流星地走了。
贾东旭看着他的背影,又回头看了看专注干活的易中海。一个张扬,一个内敛,
却都是靠着手艺在厂里立足。收工回家的路上,易中海走在前面,贾东旭跟在后面,
两人都没说话。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叠在布满车辙的土路上。进了四合院,
贾张氏已经在门口盼着了,见他回来,赶紧迎上来:“累坏了吧?饭在锅里温着呢。
”屋里的小桌上摆着窝窝头和一碗咸菜,还有一碗玉米糊糊。贾东旭坐下就吃,
贾张氏坐在旁边看着,絮絮叨叨地问:“师傅人咋样?给你派啥活了?有没有人欺负你?
”“师傅是易大爷,挺好的。”贾东旭喝了口糊糊,“就干点杂活,没人欺负。
”“那得拜师啊!”贾张氏急了,“不拜师,人家能真心教你?
你爸当年就是跟你李大爷拜了师,才学出的手艺。”贾东旭点点头。他今天看了一天,
心里早就有了数。易中海这样的手艺人,看重的不是嘴上功夫,是实在。想让他真心教,
光靠老贾的面子不够,得拿出诚意来。他啃完最后一口窝窝头,抹了抹嘴:“妈,我知道。
过两天,我备点东西,正式跟易师傅拜师。”窗外的天渐渐黑了,院里的灯一盏盏亮起来,
混着各家的咳嗽声、孩子的哭闹声,透着股烟火气。贾东旭靠在椅背上,揉了揉发酸的肩膀,
心里却很踏实。这日子,得一步一步走。第三章 拜师进厂三个月,
贾东旭渐渐摸清了车间的节奏。天不亮就往厂里赶,天黑透了才回院,
日子过得像台上了发条的钟,规律,也扎实。他不再是刚来时那个连砂纸都磨不利索的生手,
现在递工具能递到易中海手边,磨零件的边角也能做到光滑平整,
连张组长路过时都夸了句“这小子手挺稳”。易中海看在眼里,心里的秤悄悄动了。
以前在院里,他总觉得贾东旭是被贾张氏惯坏的孩子,走路都晃悠,见了人唯唯诺诺,
吃起东西来却不含糊。可这三个月下来,这小子身上的懒气褪了不少,每天来得比谁都早,
擦机床、扫铁屑,不用吩咐就干得利索,递过来的扳手永远是柄朝自己,
磨好的零件码得整整齐齐。这天午休,易中海坐在木凳上抽烟,
看着贾东旭蹲在地上擦机床底座,阳光照在他汗湿的后颈上,透着股结实的劲儿。
他心里琢磨着,自己快四十了,媳妇的肚子还没动静,虽说还想再等等,可总得留个后手。
老贾当年跟自己关系不算近,但也没红过脸,如今他儿子肯踏实干活,倒也算个靠谱的苗子。
贾东旭不知道易中海的心思,他只觉得日子比刚来时松快了些。工资发了三十三块五,
他一分不少交给贾张氏,自己只留了五毛钱买烟——不是抽,是给易中海备着。
每天给易中海打饭时,他总会多等两分钟,
等傻柱把菜汤里的油花撇到易中海的饭盒里;易中海的茶杯空了,他总能第一时间续上热水,
温度不烫嘴。这些小事做得自然,像在部队时给班长递枪一样,成了习惯。这天晚上回到家,
贾张氏正坐在灯下纳鞋底,见他进门就把针线筐往桌上一放:“东旭,你脑子咋就不开窍呢?
”贾东旭摘下工装外套,挂在墙上:“妈,咋了?”“咋了?”贾张氏瞪他一眼,
“你都进厂三个月了,还在磨零件、递扳手!易中海那手艺,你学个一招半式,
将来也能混个三级工、四级工,总比现在干杂活强!”“我天天给师傅打饭、递水,
他也没说要教我啊。”贾东旭坐下,拿起桌上的窝窝头啃了一口。“那是你没拜师!
”贾张氏急得拍大腿,“这年头手艺金贵着呢,师徒如父子,你不拜师,
人家凭啥教你真东西?你看易中海,六级工!工资是你的两倍还多,人家凭啥?
就凭手上的活!你现在是一级工,跟临时工就差个名分,想熬到六级工,猴年马月去?
”贾东旭没说话。他不是没想过,可每次看着易中海那张没什么表情的脸,
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在部队见惯了直来直去,实在摸不准这年代拜师该怎么开口。“妈,
我……我不知道咋说啊。”“我去说!”贾张氏拍板,“这周日休息,我备点东西,
咱娘俩去他家,把话说透了!”周日一早,贾张氏揣着攒了三个月的钱,
去供销社割了一斤五花肉,又打了一瓶二锅头,
回来时脸都在疼——这肉钱够买二十斤棒子面了。她把肉用麻绳捆好,酒瓶子擦得锃亮,
塞到贾东旭手里:“走,跟我去你易大爷家。”易中海家就在中院,门没关严,
透着缝能看见里面的人影。贾张氏清了清嗓子,轻轻敲了敲门:“易大哥,在家吗?
”屋里传来易中海媳妇的声音:“是大妹子吧?进来吧。”推门进去,
易中海正坐在炕沿上看报纸,他媳妇在灶台边忙活,见他们进来赶紧擦手:“大妹子来了,
快坐。”贾张氏把肉和酒往桌上一放,笑得有些拘谨:“易大哥,易大嫂,也没啥事,
就是东旭这孩子进厂多亏你照应,这点东西,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易中海放下报纸,
目光在桌上的肉和酒上扫了一眼,又看向贾东旭:“东旭,你娘的意思,你知道?
”贾东旭心里一紧,赶紧站起来,对着易中海鞠了一躬:“师傅,我想跟您拜师学艺。
”易中海没立刻答应,拿起桌上的旱烟袋,慢悠悠地装烟丝:“东旭,拜师不是小事。
进了我这门,就得守我的规矩:第一,干活要实,不能偷奸耍滑;第二,做人要诚,
不能算计街坊;第三,我教你的手艺,得传下去,但不能用它坑人。你能做到?
”贾东旭心里一热,腰弯得更低:“师傅,我能做到!”他在部队时,
班长教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手艺过硬,人品更得过硬”,易中海的规矩,合他的脾气。
易中海点了点头,对媳妇说:“把肉收起来,中午包饺子。”又看向贾张氏,“大妹子,
既然东旭认了我这个师傅,以后在厂里,我会好好教他。但丑话说在前头,
学手艺得靠自己悟,我不会手把手喂到他嘴里。”贾张氏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那是自然!
易大哥你肯教,就是东旭的福气!这孩子要是不听话,你该打打,该骂骂!”中午,
易中海家的锅里飘出饺子香。猪肉白菜馅的,贾东旭吃得格外香。
易中海给他倒了半杯酒:“尝尝?”贾东旭抿了一口,辣得直皱眉,
惹得易中海媳妇笑个不停。易中海看着他的样子,嘴角也带了点笑意:“从明天起,
你别光磨零件了,我教你看图纸。”“哎!”贾东旭响亮地应了一声,心里像揣了个暖炉。
他知道,从今天起,他在这轧钢厂,才算真正有了个奔头。吃完饺子告辞时,
贾张氏拉着易中海媳妇的手说了半天家常,全是嘱咐东旭要听话的话。贾东旭跟在后面,
看着中院的石榴树抽出了新芽,心里琢磨着,
明天该把藏在工具箱里的那本《钳工基础》拿出来,好好学学了。日子还长,但脚下的路,
好像一下子清楚了不少。第四章 相亲与缘分拜了师,贾东旭在厂里的日子更有奔头了。
易中海虽没把压箱底的手艺一股脑全教给他,却也不再让他只干杂活。
从认图纸到用游标卡尺,从简单的锉配到划线,一步步带着他入门。易中海教得严,
一个角度差了半度都得让他返工,嘴里说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手上却会放慢动作,
让他看清楚力道怎么收放。贾东旭学得也认真。下班回家,别人聚在院里闲聊,
他就把易中海给的旧图纸铺在桌上,对着煤油灯琢磨;周末休息,他也往厂里跑,
借着打扫卫生的由头,看老师傅们怎么处理复杂的活儿。一年下来,他手上的茧子厚了几层,
眼神却越来越亮,拿起锉刀时,手腕的稳劲连张组长都点头:“有点老贾的影子了。
”这天收工,易中海叫住他:“东旭,下周厂里考二级工,你去试试。
”贾东旭愣了一下:“师傅,我……能行?”“行不行试过才知道。
”易中海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这一年的底子够了,就是缺个证。去考,
考不过回来我再给你补。”考试那天,贾东旭沉着得不像个刚满十九岁的小伙子。考锉配时,
他屏着气,锉刀在工件上平稳滑动,铁屑簌簌落下,最后量出来的公差,比标准还小了两丝。
监考的师傅看了眼单子,又看了看他,难得多了句嘴:“小伙子,手挺稳。”结果出来,
贾东旭稳稳过了二级工。当天晚上,贾张氏割了二斤肉,又买了瓶酒,
拉着贾东旭去请易中海。易中海家的炕桌摆开,四个菜:红烧肉、炒白菜、凉拌黄瓜,
还有一碗鸡蛋羹,是易中海媳妇特意给东旭做的。“师傅,谢谢您。
”贾东旭给易中海倒满酒,自己也端起杯,“这杯我敬您。”易中海呷了口酒,
脸上带着笑意:“谢我干啥?是你自己肯下功夫。”他顿了顿,又说,
“我这几天也刚评上七级工,咱爷俩也算双喜临门。”贾张氏笑得合不拢嘴,
给易中海媳妇夹菜:“都是您俩照应,东旭才有今天。现在他工资涨到三十七块五,
也该琢磨个人问题了。”这话一出,易中海媳妇接了话:“可不是嘛,东旭这孩子踏实,
该找个好姑娘了。”贾张氏要的就是这句话,赶紧把心里的盘算倒了出来:“我想着,
找个本分的,手脚勤快的,最好能有份工作,哪怕是临时工呢,俩人挣钱,日子能宽裕点。
”说干就干。转天贾张氏就托了院里相熟的王大妈当媒人。王大妈在胡同里串了大半辈子,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听了贾张氏的要求,咂咂嘴:“大妹子,你这要求可不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