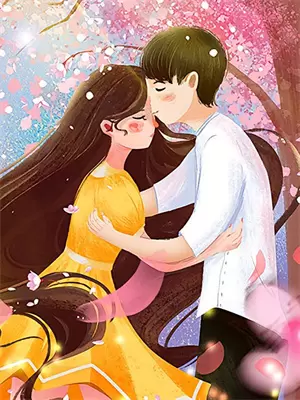林晓又一次在厨房的流理台上发现了钥匙,下面压着一张纸条:“别忘了带钥匙,家里没人。
”那熟悉的笔迹让她眼眶发热。
这是陈墨不知第几次藏起钥匙又留纸条了——他始终记得要提醒她带钥匙,却已经想不起,
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就是他曾经再三叮嘱要注意安全的那个人。“墨,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少放酱油多放糖,对不对?”林晓端着碗,
小心翼翼地走到沙发前。陈墨抬起头,那双曾经盛满智慧与温柔的眼睛如今只剩下茫然。
他礼貌地笑了笑:“谢谢你,不过我不太饿。”“就尝一口,好吗?
你以前能连吃三碗米饭就着这个红烧肉呢。”林晓努力维持着嘴角的弧度,不让它垮下来。
陈墨犹豫地接过碗,尝了一小口,点点头:“很好吃。”然后他把碗放在茶几上,
目光转向窗外,“我在等人,不能吃太饱。”林晓的心沉了下去,
但她还是柔声问:“等谁呢?”“一个很重要的人。”陈墨的眼中闪过一丝微光,
“我答应过要等她。”这样的对话几乎每天都在重复。林晓深吸一口气,
在他身边坐下:“陈墨,看着我。我就是你要等的人,记得吗?林晓,你的晓晓。
”陈墨认真地端详着她的脸,然后轻轻摇头:“不,我要等的人……她有一头长发,
总是扎成马尾,笑起来眼睛像月牙。”他顿了顿,努力在混沌的记忆中搜寻,
“她喜欢穿蓝色的裙子,转起来像一朵绽放的花。”林晓的眼泪差点夺眶而出。
他描述的是二十年前的自己,大学时代的她。“那就是我啊,墨。”她握住他的手,
“我们都老了,我剪了短发,眼角有了皱纹,但那还是我。”陈墨轻轻抽回手,
语气坚定而疏离:“女士,请不要这样。我很感激你的照顾,但我要等的人真的不是你。
”林晓终于忍不住起身冲进厨房,拧开水龙头,让流水声掩盖她的啜泣。四十三岁的陈墨,
中国最年轻的神经科学教授,半年前还被学生们崇拜地称为“行走的百科全书”,
如今却连自己的妻子都认不出来了。阿尔茨海默症——这个他们一起研究多年的疾病,
最终却找上了他本人。讽刺的是,陈墨正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他曾经开玩笑说:“要是我得了这病,晓晓你一定要狠狠地嘲笑我,
谁让我总说自己记忆力无敌呢。”当时他们谁都没料到,
这句玩笑会在几年后成为残酷的现实。林晓擦干眼泪,重新挤出笑容回到客厅。
陈墨正对着相册发呆——那是她特意制作的,
记录着他们从青梅竹马到相伴二十年的点点滴滴。“这个人,
”陈墨指着照片上穿着学士服的年轻女孩,“很像我要等的人。”“那就是我,陈墨。
”林晓指着另一张照片,“这是我们的结婚照,记得吗?在海边,
你紧张得差点把戒指掉进沙子里。”陈墨困惑地看着照片,又看看林晓,摇了摇头:“不,
不像。”林晓不甘心地翻到另一页:“那这张呢?去年我们在黄山看的日出,你说了什么,
记得吗?”陈墨的眼神恍惚了片刻,似乎有什么被触动了。他轻声说:“日出...很美。
但最美的是...是和...”他突然抱住头,表情痛苦,
“我想不起来了...”“没关系,想不起来没关系。”林晓连忙安抚他,合上相册,
“我们不看这个了。”医生说过,强迫他回忆只会增加他的痛苦。可林晓总是忍不住尝试,
就像溺水的人拼命想抓住一根稻草。晚饭后,陈墨突然变得焦躁不安,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我要回家了,太晚了晓晓会担心的。”他说。
林晓的心像被针扎了一样疼:“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啊,陈墨。你看看这些家具,
这沙发是你亲自挑的,这窗帘是我妈妈亲手做的...”陈墨停下来,环顾四周,
眼神更加困惑:“不,我的家不是这样的。我和晓晓的家...有个小院子,
她种了很多花...”那是他们刚结婚时租住的平房,早已在七年前的旧城改造中拆除了。
林晓无力地坐在沙发上。她意识到,陈墨的记忆正在一点一点地倒退,从近期到远期,
像退潮的海水,无情地卷走他们共同拥有的时光。“你睡吧,”她最终说,
“明天我带你回家。”安抚陈墨睡下后,林晓独自在阳台上哭了很久。夜风很凉,
就像她此刻的心。他们从小一起长大,从六岁到四十三岁,三十七年的时光,二十年的婚姻,
如今只剩下她一个人记得。第二天清晨,林晓被厨房里的声响惊醒。她走进厨房,
看见陈墨正手忙脚乱地煎蛋,灶台上一片狼藉。“你在干什么?”林晓惊讶地问。
陈墨吓了一跳,锅铲掉在地上。“我...我想给晓晓做早餐,”他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她今天要参加重要考试,不能饿肚子。”林晓愣在原地。他说的应该是高考那天的事。
那天清晨,陈墨确实偷偷溜进她家厨房,想为她做一顿加油早餐,结果触发了火警报警器,
弄得整栋楼鸡飞狗跳。“陈墨,看看我,”林晓轻声说,“我就是晓晓啊。
”陈墨仔细地看着她,有那么一瞬间,林晓以为他认出来了。
但他的眼神很快又变得茫然:“不,晓晓才十八岁,今天她要高考...”林晓叹了口气,
知道争辩无益。“好吧,我来帮你。”她说,接过锅铲,“晓晓喜欢单面煎的荷包蛋,对吗?
”陈墨脸上绽放出惊喜的笑容:“对!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就是...”林晓话说一半又咽了回去,改口道,“因为我是她的朋友啊。
”他们一起做了早餐,陈墨吃得津津有味。看着他满足的样子,林晓的心既痛又暖——至少,
他还记得要对她好,哪怕对象已不是眼前的她。饭后,陈墨突然紧张起来:“几点了?
我得去接晓晓,考试快结束了。”林晓看了眼时钟,柔声说:“还早呢,你先休息一下,
我去接她,好吗?”“不,我得亲自去。”陈墨固执地说,“我答应过要在校门口等她,
手捧一束向日葵。”林晓的眼泪终于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他记得,他都记得!
只是不记得她已经老了,不记得她就站在他面前。“好,我们去接她。”林晓擦干眼泪,
决定陪他演完这场戏。
他们开车来到陈墨记忆中的高中母校——如今这里已经是一所实验中学了。
陈墨焦急地站在校门口,手里攥着林晓临时从花店买来的向日葵。“她怎么还不出来?
”陈墨不停地看表,“是不是考得不好,躲在教室里哭了?”林晓记得那天,
她确实考砸了数学,最后一个走出考场,看见陈墨捧着向日葵站在夕阳里,
她扑进他怀里哭了很久。而他一直安慰她,说没关系,说无论如何他都陪着她。
“她会出来的,再等等。”林晓轻声说。天色渐暗,校门口的人群早已散去。
陈墨手中的向日葵耷拉着脑袋,像他一样沮丧。“她是不是不来了?”陈墨的声音带着哭腔。
林晓看着他失落的样子,心如刀割。她拿出手机,找到自己十八岁时的照片,
递到他面前:“你看,晓晓已经回家了,她让我告诉你,别等了。”陈墨盯着照片看了很久,
眼神从困惑到恍然:“真的...回家了?”“嗯,回家了。我们也回去吧。
”陈墨终于点点头,任由林晓牵着他的手走向车子。上车前,
他回头望了一眼空荡荡的校门口,轻声说:“她平安就好。”回家的路上,陈墨睡着了。
林晓不时从后视镜里看他安静的睡颜,泪水一次次模糊视线。她不得不把车停在路边,
让自己哭个够。这种折磨何时才是尽头?每天面对最亲爱的人,
却被他当作陌生人;每天重复着“我就是你要等的人”,却只换来礼貌而疏离的回应。
几周后的一个雨夜,林晓被雷声惊醒,发现陈墨不在身边。她慌忙起身寻找,
最后在书房里找到了他。陈墨坐在书桌前,台灯亮着,他正专注地看着什么。林晓走近,
发现那是他们的结婚相册。“你...”林晓一时不知该说什么。陈墨抬起头,
眼中是她许久未见的清明。“晓晓,”他轻声唤道,那熟悉的语气让林晓浑身一震,
“我想起来了,一点点。”林晓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记得我了?
”“不是全部,”陈墨摇摇头,手指轻抚相册上两人的笑脸,“但我知道,
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这些照片...我感觉很熟悉。”林晓跪在他身边,
握住他的手:“对,我是你的晓晓,你的妻子。
”陈墨的眼中涌出泪水:“对不起...我总是不记得你...”“没关系,真的没关系。
”林晓也哭了,“只要你偶尔能像现在这样,想起一点点,我就很满足了。”那一夜,
他们相拥而眠,像从前一样。林晓第一次睡得如此安稳,仿佛回到了陈墨生病前的日子。
然而第二天早晨,残酷的现实又回来了。“早上好,”陈墨礼貌地对厨房里的林晓说,
“请问...你是?”林晓手中的锅铲差点掉落。昨夜的温情时刻如昙花一现,
今天的他又回到了那个只记得要“等一个很重要的人”的状态。但她没有放弃。
在陈墨吃早餐时,林晓拿出手机播放他们最喜欢的歌曲——那是他们大学时代常听的乐队,
早已解散多年。陈墨停下筷子,侧耳倾听。“这旋律...很熟悉。”他说。“记得吗?
大三那年,你省吃俭用买了他们的演唱会门票,我们偷偷溜出学校,
坐了一夜的火车去北京...”林晓轻声讲述着。陈墨努力地听着,眉头紧锁,
仿佛在迷雾中寻找出路。“北京...火车站...很冷...”“对!那天下雨了,
我们只带了一把伞,你的半边身子都湿透了。”林晓激动地说。陈墨的眼中闪过一丝光芒,
但很快就熄灭了。“我想不起来了。”他沮丧地放下筷子,“我的头很痛。
”林晓连忙关掉音乐:“不想了,我们不想了。吃饭吧。
”这样的时刻越来越多——短暂的清醒,随即是更长的迷茫。
就像溺水的人偶尔浮出水面吸一口气,然后又沉入深海。有一天,林晓在整理陈墨的书桌时,
发现了一个笔记本。翻开第一页,她愣住了。“如果我忘记了你,请原谅我。
”那是陈墨的笔迹,略显颤抖但依然可辨,“但我知道,即使我忘记了全世界,
也不会停止爱你。”林晓一页一页地翻下去,发现这是陈墨在病情初期写的日记。
那时候他刚刚确诊,还没有告诉她真相。“今天医生确认了,阿尔茨海默症。多讽刺,
我研究了半辈子这个病,最终却要亲身体验。最痛苦的不是自己会忘记,而是会让晓晓痛苦。
”“我开始记录我们的故事,趁我还记得。从六岁相识那天起,她扎着两个小辫子,
递给我一半橡皮擦。”“今天我第一次忘了她的生日。看着她失望但强装不在乎的表情,
我的心比知道病情时还要痛。”“我决定告诉她了。不能再瞒下去。看着她崩溃的样子,
我恨不得这病立刻夺走我所有记忆,至少不用面对她的眼泪。”林晓瘫坐在地上,泣不成声。
原来陈墨独自承受了这么多,原来他早就开始为这一天做准备。
日记的最后一页写着:“如果我连你也认不出了,晓晓,请记住:不是我不爱你了,
只是我的大脑关上了那扇门。但爱在心里,不在脑中。你要继续生活,连同我的那一份。
”那天晚上,林晓把日记本放在陈墨面前。“看看这个,好吗?这是你写的。
”陈墨犹豫地翻开,一页一页地看着,表情从困惑到专注,再到痛苦。“这...是我写的?
”他问。林晓点头:“是你生病初期写的,为了我。”陈墨沉默了很久,
然后轻声说:“这个人很爱你。”“那就是你啊,陈墨。”林晓握紧他的手。
陈墨却摇摇头:“不,那是过去的我。现在的我...配不上这样的感情。”林晓的心碎了。
她终于明白,最痛苦的不是被他忘记,而是看着他因为忘记而痛苦自责。随后的日子里,
陈墨的状况持续恶化。他开始忘记如何系鞋带,如何刮胡子,甚至有时候会忘记吃饭。
但他始终记得要“等一个很重要的人”。林晓不再执着于让他认出自己。
她开始以看护者的身份陪伴他,
偶尔讲述“那个他要等的人”的故事——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的故事。“她是个怎样的人?
”有一天陈墨突然问。林晓愣了一下,随即微笑:“她很爱你。从六岁起就爱你,
至今没有改变。”“那她为什么不来见我?”陈墨像个失落的孩子。林晓深吸一口气,
轻声说:“她每天都在你身边,只是你认不出她了。”陈墨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不再追问。
冬天来临时,陈墨感染了肺炎,住进了医院。林晓日夜守在病床前,握着他日渐消瘦的手。
“晓晓...”一天深夜,陈墨在睡梦中喃喃呼唤。林晓立刻惊醒:“我在这里,墨。
”但陈墨并没有醒来,
只是在梦中继续呓语:“别走...等我...”林晓把脸埋在他的手心里,
泪水浸湿了床单。即使在梦中,他也在寻找她。肺炎痊愈后,陈墨的身体大不如前。
医生说他需要专业护理,建议送他去专门的机构。林晓拒绝了:“我答应过,
无论如何都会陪在他身边。”回家后的陈墨更加沉默,常常一整天不说一句话。
但他会紧紧跟着林晓,无论她走到哪个房间,他都像影子一样跟在后面。
“你为什么总是跟着我?”有一次林晓忍不住问。陈墨认真想了想,说:“不知道。
但感觉...不能让你离开我的视线。”林晓忽然明白了——在他的内心深处,
在那个被疾病遮蔽的角落,他依然认得她,依然想要守护她。除夕夜,
林晓做了丰盛的年夜饭,还特意包了饺子——陈墨最爱的韭菜馅。窗外烟花绽放,
映亮了陈墨的脸。他望着夜空,忽然说:“晓晓喜欢烟花。”林晓手中的筷子顿住了。
这是几个月来他第一次主动提起“晓晓”。“是啊,她最喜欢烟花了。”林晓轻声回应。
“有一年...我买了很多烟花,在她家楼下放。”陈墨努力地组织着语言,
“她笑得...很漂亮。”林晓记得那个新年夜。陈墨用半个月的兼职薪水买了一大箱烟花,
在她家楼下放给她看。邻居差点报警,但她觉得那是世界上最浪漫的事。
“如果...如果你见到她,”陈墨转向林晓,眼神异常清明,“请告诉她,我永远爱她。
即使...即使我忘记了她的样子。”林晓的眼泪夺眶而出:“她知道的,陈墨。
她一直都知道。”陈墨满意地点点头,继续看窗外的烟花。那一刻,林晓忽然释然了。
认不认出她又如何?他们的爱早已超越了记忆,成为了本能。就像他会提醒她带钥匙,
会想为她做早餐,会记得她喜欢烟花——这些深入骨髓的习惯,比记忆更持久。那天晚上,
陈墨睡得很安稳。林晓躺在他身边,听着他均匀的呼吸声,忽然明白了爱的真谛。
不是被记得,而是去记得;不是被爱,而是去爱。清晨,阳光透过窗帘洒进卧室。陈墨醒来,
看见身边的林晓,露出了久违的温柔微笑。“早上好,”他说,然后顿了顿,轻声加了一句,
“晓晓。”林晓愣住了,生怕一动就会打破这个梦境般的时刻。林晓手里的碗差点没拿稳,
热汤洒了出来,烫红了她的手背。可她感觉不到疼,只是死死盯着陈墨。
“你...你刚才叫我什么?”陈墨的眼神依然茫然,
但嘴角却挂着一丝温柔的弧度:“晓晓。你是晓晓,对吗?”林晓扑到床边,
颤抖着握住他的手:“是,我是晓晓,你的晓晓。”陈墨轻轻摸着她的短发,
像抚摸什么易碎的宝贝:“你的头发...怎么短了?”“因为你说过喜欢我短发的样子。
”林晓哽咽着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这是半年来陈墨第一次认出她。不是通过照片,
不是通过提醒,而是真真切切地认出了眼前的她。陈墨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然后又摇摇头:“我好像...睡了很久。”“没关系,醒了就好。
”林晓把脸埋在他手心里,感受着他掌心的温度。那天早晨,陈墨异常清醒。
他记得林晓最爱吃的菜,记得她最讨厌下雨天,甚至记得她十八岁生日时许的愿望。
“你说要永远和我在一起,”陈墨微笑着说,“你看,愿望成真了。”林晓又哭又笑,
不停地点头。她给医生打了电话,医生说这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偶尔会出现的“清明时刻”,
但提醒她不要过于乐观。林晓才不管这些。她珍惜每一秒,把陈墨扶到客厅,打开相册,
指着照片一张张讲解。“这是我们大学毕业那天,
”她的手指轻轻划过照片上两个笑容灿烂的年轻人,“你当时说,
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娶我了。”陈墨专注地看着,眼神温柔:“你穿着白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