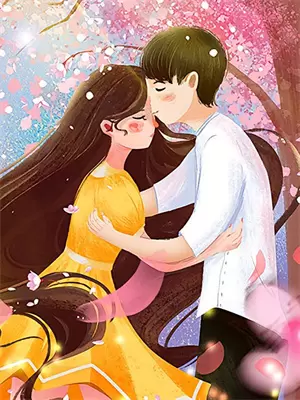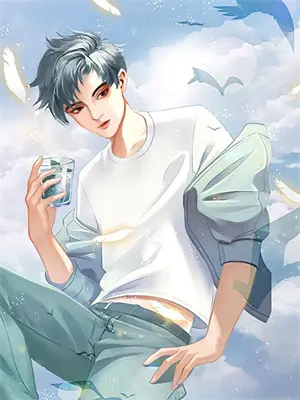
林深是在一个暴雨将至的午后,收到那封信的。出租屋的窗户正对着一片老旧居民楼的后墙,
墙面上爬满了枯萎的藤蔓,像一道道丑陋的伤疤。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尘土味,
混杂着楼下小吃摊飘上来的油烟,黏腻得让人喘不过气。林深瘫坐在地板上,
背靠着冰冷的墙壁,面前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
是他删改了不下五十遍的小说开头——“城市的霓虹像一场永不落幕的骗局”。
这句话像一根刺,扎在他荒芜的思绪里,拔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距离出版社的截稿日期只剩三天,他的新书《无声的轰鸣》依旧是一片废墟。半年前,
他辞掉了广告公司文案的稳定工作,揣着父母半生积蓄和自己所有的勇气,
一头扎进这座号称“梦想之都”的城市,发誓要写出一本能让文坛震动的小说。
可现实给了他最响亮的耳光:积蓄早已见底,房租拖欠了两个月,
编辑的催稿电话从最初的耐心询问变成了最后的冰冷警告,连楼下卖馄饨的张叔看他的眼神,
都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同情。他抬手摸了摸烟盒,里面空空如也。
烦躁地将烟盒揉成一团扔向垃圾桶,却没扔中,纸团撞在墙角,弹了回来,像个嘲讽的笑脸。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轻微的“叩叩”声,不是房东那沉重的砸门声,
倒像是怕惊扰了什么似的。林深起身,透过猫眼往外看。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一片漆黑,
什么也看不见。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拉开了门。门口空无一人,
只有一只被雨水打湿了一角的牛皮纸信封,静静地躺在冰冷的地板上。信封没有邮票,
也没有寄信人地址,只在正中央用蓝黑墨水写着一行字:“给需要一点光的人”。
字迹算不上工整,笔画有些颤抖,甚至有几个字的墨渍晕开了,却透着一股执拗的认真,
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写上去的。林深弯腰捡起信封,指尖触到那粗糙的纸张,
心里莫名地动了一下。他本不想理会这封来历不明的信,城市里的骗局太多,
他已经没有精力去分辨真假。可那行“需要一点光”像一根细小的针,
精准地刺中了他内心最脆弱的地方——他现在,太需要一点光了。关上房门,
他将信封放在桌上,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窗外的雷声越来越近,一道惨白的闪电划破天际,
瞬间照亮了整个房间,也照亮了他眼底的疲惫和迷茫。他深吸一口气,拆开了信封。
里面是三张泛黄的信纸,纸张边缘已经有些磨损,像是被人反复摩挲过。
字迹和信封上的一样,带着泥土般的质朴,偶尔还有几个错别字,却写得密密麻麻,
填满了整个纸面。“你好,我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寄到你手里。
我叫陈阿婆,住在山坳里的老槐树下。昨天我家的猫丢了,它叫‘团子’,是只三花猫,
右耳朵缺了一小块,尾巴尖还有点白毛。我找了它一整天,从后山的竹林找到村头的小溪,
嗓子都喊哑了,也没看见它的影子。”“我这把老骨头了,腿脚不方便,
爬到半山腰就喘得不行。天黑的时候,我坐在石头上哭,风把眼泪吹干了,
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是少了一块肉。团子很乖,从不乱跑。每天我做饭的时候,
它就蹲在灶台边,眼睛亮晶晶地盯着锅,等着我给它丢一块小鱼干。晚上我看电视,
它就蜷在我的腿上睡觉,呼噜声比电视声还响。它就像我的家人一样,不,它就是我的家人。
”“我没有儿女,老伴走得早,这房子里就我和团子两个人。以前还有邻居家的孩子来串门,
后来他们都搬去城里了,山坳里就越来越冷清。团子丢了,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
夜里我睡不着,听着窗外的虫鸣,总觉得那声音里都带着哭腔。后来我想,不如写封信吧,
写给一个和我一样,心里有点空落落的人。如果你收到了,就当是听一个老太婆说说话,
别嫌我啰嗦。”信纸的边缘有些湿润的痕迹,像是眼泪打湿后又风干的印记。林深捏着信纸,
指尖有些发凉。他想起了自己的父母,半年没联系了,上次通电话时,
母亲在那头哭着劝他回家,说“实在不行就找个安稳工作,爸妈养得起你”,
他却不耐烦地挂了电话,说他们不懂自己的梦想。现在想来,那些所谓的梦想,
不过是自己逃避现实的借口。他以为逃离了家乡的小县城,就能在大城市里闯出一片天,
却没想到,最终只是把自己困在了一个更小的出租屋里,连抬头看看天的勇气都没有。
暴雨终于倾盆而下,砸在窗户上噼啪作响,像是要把这座城市的虚伪和冷漠都冲刷干净。
林深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外面模糊的城市夜景。霓虹灯闪烁,却照不亮他心里的阴霾。
他突然觉得,自己和那个丢了猫的陈阿婆一样,都是被世界遗忘的人,
在黑暗里独自舔舐着伤口。接下来的两天,林深依旧对着电脑发呆,
却总会时不时想起那封信。他开始好奇,那个住在山坳里的陈阿婆,后来找到她的团子了吗?
她一个人住在山里,会不会很孤单?夜里会不会害怕?截稿日的前一天,林深还是一字未写。
他索性关掉电脑,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外套,走出了出租屋。雨已经停了,
空气里带着泥土的清新,却依旧驱散不了他心里的沉闷。他漫无目的地走着,
不知不觉来到了一个老旧的邮局门口。邮局的招牌已经褪色,玻璃门上贴着几张泛黄的海报,
上面的字迹都有些模糊了。看着“邮政”两个字,林深突然有了一个念头。
他转身走进旁边的文具店,买了一本方格信纸和一个牛皮纸信封,
然后在邮局门口的长椅上坐了下来。“陈阿婆您好,我收到了您的信。”他握着笔,
笔尖悬在纸上,迟迟没有落下。他不知道该写些什么,
不知道自己的安慰会不会显得苍白无力。他甚至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寄到陈阿婆手里。
犹豫了很久,他才慢慢写下:“我也不知道团子在哪里,但我相信,它一定还记得您的好,
说不定只是迷路了,很快就会回家的。就像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在人生的路上迷路,
但只要心里还有牵挂,就总能找到回家的路。”“我最近也遇到了一些麻烦,心情很不好,
觉得自己特别没用,甚至想过放弃。看到您的信,我突然觉得没那么孤单了。
原来不止我一个人在黑暗里挣扎,还有您,还有团子,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人,
都在努力地活着。”“我没有见过团子,但我能想象出它的样子,一定很可爱。您别太担心,
说不定等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它已经回到您身边,正蹲在灶台边等着您给它丢小鱼干呢。
”他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只是在信封上写了“山坳里老槐树下 陈阿婆收”。
他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寄到,只希望能给那个素未谋面的老人带去一丝安慰,
就像她的信给了他一丝温暖一样。把信投进邮筒的那一刻,林深心里莫名轻松了一些。
他抬头看了看天,乌云已经散去,露出了一小块湛蓝的天空。他转身离开邮局,
脚步也轻快了几分。回到出租屋,林深打开电脑,手指放在键盘上。这一次,他没有再犹豫,
那些憋了很久的文字,终于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他写城市的冷漠,写梦想的破碎,
写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也写那些藏在角落里的温暖和善意——就像陈阿婆的信,
就像他此刻的心情。三天后,林深按时把稿子交给了编辑。他没有抱太大希望,
甚至做好了被退稿的准备。却没想到,一周后,编辑的电话打了过来,
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兴奋:“林深,你的稿子通过了!出版社决定出版,
而且我们很看好这本书,准备重点推广!”林深拿着手机,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
他激动得手都在抖,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了下来。他想起了陈阿婆的信,想起了自己写的回信,
想起了那些在黑暗里挣扎的日子。他觉得,是那封信给了他勇气,
让他重新找回了写作的信心,也让他明白了,生活再艰难,也总有一束光在等着他。
他决定去一趟陈阿婆住的地方,亲自感谢她。他按照信封上模糊的地址,
先坐火车到了邻省的一个小县城,然后转乘大巴到了乡镇,最后雇了一辆三轮车,
沿着蜿蜒的山路往山坳里走。山路很崎岖,三轮车颠簸得厉害,林深的骨头都快散架了。
但他一点也不觉得累,心里充满了期待。山路两旁是茂密的树林,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形成一道道金色的光斑。空气里弥漫着青草和泥土的清香,
耳边是鸟鸣和风吹树叶的声音,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无比放松。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
三轮车停了下来。车夫指着前面一条狭窄的小路说:“前面就是老槐村了,
你沿着这条路走十分钟,就能看到那棵老槐树了。”林深付了钱,谢过车夫,
沿着小路往前走。小路两旁是一片片农田,田里种着水稻和蔬菜,几个农民正在田里劳作,
看到林深,都好奇地看了过来。林深笑着点了点头,继续往前走。很快,
他就看到了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槐树,树干粗壮,需要两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合抱过来。
槐树下有一座小小的木屋,屋顶盖着瓦片,烟囱里飘出袅袅炊烟。
一个头发花白的阿婆正坐在门口的竹椅上,手里拿着针线,似乎在缝补一件旧衣服。
她的身边,卧着一只三花猫,右耳朵果然缺了一小块,尾巴尖的白毛在阳光下格外显眼。
“阿婆您好。”林深走过去,轻声说道。阿婆抬起头,看到林深,有些惊讶:“你是?
”她的声音有些沙哑,却很温和。“我是收到您信的人。”林深笑着说,“我叫林深,
来看看您,还有团子。”阿婆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了笑容,
脸上的皱纹像绽放的菊花:“原来是你啊!快进来坐,快进来坐。”她放下手里的针线,
站起身,想要给林深倒水。“阿婆您坐着,我自己来就行。”林深连忙拦住她,
“您身体不好,别累着。”阿婆笑着点了点头,重新坐回竹椅上:“不碍事,老毛病了。
团子后来自己回来了,还带回了一只小猫咪呢,你看。”她指了指团子的肚子下面,
那里果然卧着一只巴掌大的小猫,毛色和团子一模一样。林深蹲下身,轻轻摸了摸团子的头。
团子很温顺,眯着眼睛,发出了“呼噜呼噜”的声音。小猫有些怕生,缩在团子的怀里,
偷偷地打量着林深。“真好,回来了就好。”林深笑着说,心里涌起一股暖流。“是啊,
回来就好。”阿婆叹了口气,“那天我收到你的信,正坐在门口哭呢。看到你的信,
我就觉得,团子一定会回来的。没过两天,它就真的回来了,还带着这么个小家伙。
”林深走进屋里,屋里很简陋,却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张老旧的木桌,几把椅子,
一个土灶台,墙角堆着一些柴火。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男人和一个女人,应该是阿婆的老伴。“阿婆,您一个人住在这里,
会不会很孤单?”林深坐在椅子上,看着阿婆问道。阿婆摇了摇头:“以前会,
现在有团子和这小家伙陪着,就不孤单了。而且还有你,给我写信,来看我。”她顿了顿,
又说:“你写的信我看了很多遍,每次看都觉得心里暖暖的。你说的对,只要心里有牵挂,
就总能找到回家的路。”林深心里一酸,说:“阿婆,其实我应该谢谢您才对。
您的信让我重新找回了信心,我的小说也出版了。”“真的?那太好了!
”阿婆高兴得拍了拍手,“我就知道,你是个有本事的人。以后肯定会成为大作家的。
”那天,林深和阿婆聊了很久。他知道了阿婆年轻的时候是村里的小学老师,教了一辈子书,
后来老伴走了,学生们也都长大了,搬去了城里,她就一个人守着这座老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