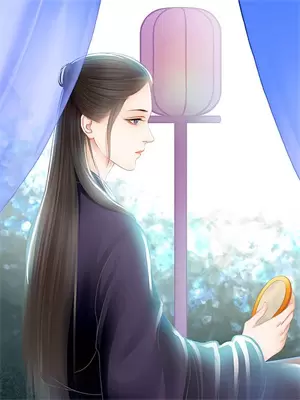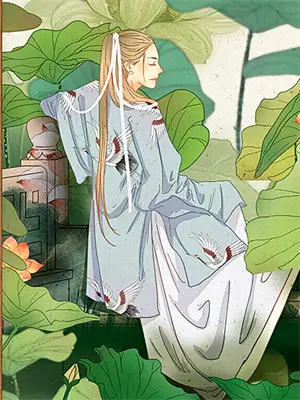
我们村闹僵尸,请来的道士说必须用活人献祭。村里抓阄选中了隔壁的孤女阿秀。
她跪在地上磕头:“我把粮食都给你们,放过我吧。”没人理她,
她被绑着扔进了后山的山洞。第二天,阿秀回来了,浑身是血,却笑容甜美。“山神说,
只要每天送一个人进去,它就不吃我。”村里开始每天死一个人,死状凄惨。一个月后,
阿秀站在祠堂前笑着问:“接下来,轮到谁呢?”---雨点敲打着破旧的窗棂,屋里,
油灯的光晕在潮湿的空气中艰难地摇曳。“听。” 年轻的后生阿茂猛地抬起头,
脸色在灯光下惨白,“又来了,那鬼声音。”他对面的老猎人德山叔蜷在炕沿,
浑浊的眼睛盯着几乎要熄灭的火焰,一动不动。他手里的旱烟袋早已没了火星。
“呜……嘎吱……咕……” 一种低沉、黏腻的咀嚼声,混在永无止境的雨声里,
从后山的方向隐隐约约传来,听得人牙根发酸,脊背发凉。“德山叔!
这村子……这村子真的完了!” 阿茂的声音带着哭腔,“三个月了!鸡鸭猫狗,
连个耗子都见不着了!除了这该死的雨,就是这……这吃骨头的声音!
”德山叔终于动了动干裂的嘴唇,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槐树上那三个,
烂得快只剩骨头了。”“他们说是狼……”阿茂急切地接话,却又自己否定,
“可狼怎么能……”“王老栓呢?”德山叔打断他,眼皮抬了抬,那眼神深得像井,
“你亲眼见过他炕上的样子。门窗,可是从里面闩得死死的。”阿茂猛地打了个寒噤,
仿佛又看到了那副惨状,胃里一阵翻腾:“肠子……流了一地……可是,什么东西能进去?
又怎么出去的?”他抱紧双臂,声音压得极低,仿佛怕被门外的什么东西听去,“叔,你说,
那……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德山叔缓缓摇头,目光重新投向窗外无边的黑暗和雨幕。
“不知道。但它就在后山,没走。而且……”他顿了顿,咀嚼声恰在此时随风清晰了一瞬,
又微弱下去,“……它一直在吃。”阿茂的脸上彻底没了血色,
他绝望地看着德山叔:“那我们怎么办?就这么等着?等着它……找上门来?
”德山叔没有回答。沉默在两人之间蔓延,比屋外的雨更冰冷,比后山的咀嚼声更让人窒息。
油灯猛地爆了一个灯花,光影剧烈一晃,仿佛真的要被这沉重的湿气和黑暗吞没了。
不是野兽。是更邪门的东西。“煞鬼……”辈分最长的七叔公蜷在祠堂角落的草堆里,
嘴唇哆嗦着,浑浊的老眼盯着跳动的灯焰,“是煞鬼……冤死的魂,
借了不干净的身子回来了……要索命,要吃东西……”没人敢接话。祠堂里挤满了人,
男人蹲在地上,闷头抽着旱烟,烟雾呛人,女人搂着吓丢了魂的孩子,
低声啜泣被死死压在喉咙里。空气里弥漫着恐惧和一种更深的东西,一种黏腻的,
正在悄悄发酵的恶意。“得想个法子!”李屠户猛地站起来,他壮实得像头牛,
此刻眼珠子却布满血丝,声音又粗又哑,“再这么下去,全村都得玩完!七叔公,
您老经的事多,祖宗就没传下什么说法?”七叔公茫然地摇了摇头,
枯瘦的手指攥紧了脏污的衣角。“或许……得请人看看。”角落里,一个微弱的声音说。
是村西头的张秀才,村里唯一的识字人,脸色苍白得像张纸。请人。请谁?这年月,
兵荒马乱,官府早没了影,能请的,只有那些游方的,有些说不清道不明本事的道士和尚。
死马当活马医。两天后,张秀才领着一个人回来了。那道士干瘦,
穿着一件分辨不出原本颜色的道袍,尖嘴猴腮,一双眼睛却亮得瘆人,看人的时候,像锥子。
他没说自己叫什么,从哪来。就在祠堂前,冒着渐渐沥沥的小雨,他摆开了阵势。
一张破桌子,几只缺口的碗,画了些鬼画符。他舞弄着木剑,嘴里念念有词,
跳了大半个时辰,然后猛地一定,手指掐算,脸色“唰”地变得惨白。“好凶的煞气!
”他声音尖利,划破了雨幕,“这东西,是横死之人的怨念所化,聚而不散,已成气候!
它饿得很,普通的牲口祭品,填不饱它的肚子!”人群骚动起来,不安像水波一样扩散。
“那……那咋办?”村长,一个老实巴交了一辈子的老汉,颤声问。
道士的目光缓缓扫过在场每一张惶恐的脸,那目光冰冷,带着一种审视牲口般的意味。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清晰地吐出:“活祭。”“须得一个活人,心甘情愿……或者,
至少是身负‘因果’之人,献与它,方能暂平其怨愤,保一方安宁。”活人!
这两个字像两块冰,砸在每个人的心口,瞬间冻结了所有的声音。祠堂前死一般寂静,
只有雨点打在瓦片上,啪嗒,啪嗒。用谁的命,去填这个无底洞?
低声嘟囔了一句:“外姓人……总归不是咱一条心……”像一颗火星掉进了浸透油的干草堆。
“对,外姓人!”“阿秀……她就一个人……”“她爹妈死得早,
谁知道是不是带了什么不干净……”“去年刘老歪死,她就从旁边过……”低语声渐渐汇聚,
变得清晰,变得理直气壮。所有的目光,或明或暗,或贪婪或躲闪,都投向了人群最后方,
那个蜷缩在屋檐阴影下的瘦小身影。阿秀。她约莫十六七岁,穿着一身打满补丁的粗布衣服,
洗得发白,低着头,枯黄的头发遮住了大半张脸,身子在微微发抖。
她是十多年前跟着逃荒的父母流落到这里的,没多久爹娘就先后病死了,她吃着百家饭,
穿着百家衣长大,沉默得像块石头,干着最脏最累的活计,仿佛天生就该是村里的一个影子,
一个物件。现在,这个物件,似乎有了最适合的用途。 低语声汇成了潮水,
涌向角落里的阿秀。她把自己缩得更紧,像一只受惊的幼兽。“总得有个法子!
” 李屠户猛地吼了一嗓子,他庞大的身躯堵在门口,脸上横肉因为激动而抖动,
“这么耗下去,大家都得死!抓阄!” 他环视众人,眼神带着逼迫,“全村成年男女,
一个不漏!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公平!”“公平”两个字从他嘴里喊出来,
带着一股血腥气。人群静了一瞬,随即被更乱的窃窃私语填满。“抓……抓阄?
”“这……”“也……也只能这样了……”没人明确反对。
恐惧已经磨掉了大多数人的思考和良知。老村长嘴唇哆嗦着,浑浊的眼睛看了看李屠户,
又看了看阴影里的阿秀,最终像被抽干了力气,颓然地点了点头,
发出一声几乎听不见的叹息:“……就……依了吧。”写好的纸条被揉成团,
扔进一个积着灰尘的黑陶罐里。只有一张,上面用干涸的朱砂,
画了一个小小的、刺眼的圆圈。人们排着队,呼吸粗重,一个接一个将手伸进那漆黑的罐口。
摸索,抽出,急切地展开。“空的!”“我没事!”“我也是空的!
”每一声带着庆幸的低呼,都像一块石头,砸在尚未抽签的人心上,
也砸在阿秀单薄的脊背上。庆幸之后,那些目光便不约而同地,带着隐秘的催促和压力,
投向队伍最后方。终于,轮到阿秀了。前面的人都刻意让开了一点,形成一个半圆,
沉默地注视着她。她的手很瘦,指节因为常年洗衣、砍柴而显得粗大凸出,
此刻正不受控制地颤抖着。她低着头,慢慢将手伸进冰冷的陶罐。罐子里,
只剩下最后一张纸条。她捏住它,像捏住一块烧红的炭。慢慢地,极其缓慢地抽了出来。
所有的眼睛都死死盯住她手中那个皱巴巴的纸团。她颤抖着,一点点展开。纸条上,
一个猩红的小圆圈,像一只突然睁开的、充满恶意的眼睛,死死地瞪着她!
阿秀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变得惨白如纸。她猛地抬起头,枯黄的头发向后滑去,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