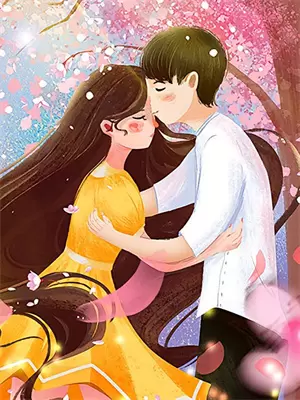第一章:我只是想要一个能亮整晚的手电筒我叫江婉清。我曾是一名“志愿测试员”,
签了一个没人关心的免责协议,住进了全市最神秘也最臭名昭著的实验基地:先锋研究中心。
人们私下都管它叫“A厂”。那时候我天真到以为,签一份协议,
就能换一个“能亮一整晚”的手电筒。但谁能想到,
这一步会让我从一个扫地打杂的小实习生,变成整个A厂主控系统的意识中枢。
我最后一次“醒来”,不是从梦中醒,而是从实验舱中醒。监控光标对准我,警报静音,
系统等待我的指令。我不再是人类的一份子了。但这一切,要从我五岁那年说起。那年,
我跟我妈去了一场展览。地点是虹东工人文化宫,
名字叫得响亮——“先锋实验技术成果展”,其实就是A厂搞出来的一次市政层面的公关秀。
我妈是市区机关干部,展会门票是单位发的,说什么“亲子科技周”。但我当时一点不开心。
场馆闷热,人太多,我一小孩挤在人堆里喘不上气,脚都快被踩扁。我记得那年很热。
那种让人全身黏腻的湿热,一直黏到我脑子里。直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感觉。
展厅正中是一条刷满橙色涂层的跑道,有个工作人员把一个铁块推了上去,
结果那东西就像打了滑油一样,飞了老远。人群“哇”地叫出声,一些孩子吓得当场哭了。
我也吓到了,死死扒住我妈的胳膊不敢动。可我妈却兴奋得很,说:“你看你,胆子真小,
人家都敢玩。”我不吭声。直到我看到边上有个展台,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女研究员,
正举着一个灰白色的手电筒。她对人群介绍:“我们最近试制了一批高能量密度电芯,
这支手电筒,一次充满,可以连续照明16小时以上。
特别适合夜间巡逻、野外驻守、或者……怕黑的小朋友。”我猛地就被吸引住了。
我确实怕黑。怕到每晚都要开床头灯。可床头灯一开,我妈就骂我浪费电,说电费贵,
不准开整晚。“我想要那个。”我扯着她的袖子说,“我要那个手电。”“那个不卖,展品。
”“我怕黑……床底下晚上有东西,它看着我。我想要那个灯。
”我妈脸色不好看了:“别胡说八道。哪来的东西?你一个女孩子整天神神叨叨的。
”“真的有!”我急得快哭出来了,“我晚上根本睡不好,它会看我,会动。
”那女研究员忽然转过头,蹲下来跟我说:“你真的很怕黑,是吗?”我点头如捣蒜。
她笑了笑,把手电筒递给我:“那你拿去好了。但要等一下——”她抬头朝一边招了招手。
一个摄影师举起相机,咔哒一声,拍下我接过那支手电的样子。我当时高兴坏了。
根本没想别的,抱着手电那晚睡得无比安稳。第二天清早,
我妈像疯了一样拿着当天的晨报进门,报纸头版照片正是我和那个女研究员,
她把手电交给我的画面清清楚楚。“你知道你昨天见到的是谁吗?
那女人就是先锋研究中心的核心人物——沈兰,是总负责人沈克文的夫人!
你怎么就能乱拿东西?你知道你上了哪张报纸吗!”我没听进去。我只记得那灯亮了一整夜。
没黑,也没鬼。我告诉她:“我想长大以后,做她那样的人。”可我不知道,
等我真的长大了,沈兰却亲手把我推进了那个没人能走出来的测试舱。
第二章:全世界都说A厂疯了,只有我不信那场展览之后,
我的生活并没有发生什么“逆天改命”的奇迹。我依旧是江婉清,
城市边缘中学里成绩中上的学生,一个被班主任评价为“有点自闭、想法奇怪”的女生。
除了那支被我用到完全失效的手电筒之外,我跟沈兰再也没联系过。但那天的照片,
一直被我偷偷剪下来,夹在作业本的最后一页。
每次被同学孤立、被老师冷眼、被亲戚问“你读书是要干嘛的”时,我就拿出来看一眼。
我告诉自己,总有一天,我也会站在她的位置上。初三那年,A厂出了大新闻。那年夏天,
电视上的新闻密集报道:“先锋研究中心多起实验引发社会关注,
大量‘志愿测试者’出现严重后遗症,甚至失踪,目前市政督查组已介入调查。
”我爸妈当时对着晚饭的热汤一边喝一边骂:“这不就是以前搞人体实验那个厂子吗?
该关早就该关。”“那群研究员不把人当人,早晚出事。”我扒饭的动作慢了下来,
眼神盯着电视上晃动的画面。片子里出现了那条熟悉的橙色跑道。还有——沈兰。
她站在记者面前,不说话,只是看着镜头,那眼神像隔着屏幕都能冻死人。
我爸哼了一声:“装什么清高。我听人说她老公早年搞研究时差点死在实验台上,
现在她是A厂的顶头人,风评一直不好。”我夹了口菜,突然开口:“我以后想去A厂。
”话一出口,整个饭桌静了几秒。我妈当场把筷子一拍:“你是不是疯了?
”“你脑子进水了?你还记不记得那厂子闹出过多少人命官司?”我很平静地说:“我记得。
但我觉得科学不是靠‘安全’堆出来的。”我爸皱眉:“别给我讲那套理想主义。
你要真想学科研,你好好考大学就行。别学那些什么高危测试员,命都没了。”我没再说话。
但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抱着那早已不亮的手电筒,脑子里想的不是实验事故,
也不是失踪的测试者。我在想:如果没有人去做那第一步实验,
那些后来能救千万人命的技术,能存在吗?如果我去了那里,
是不是……也能做出一点点改变?我不知道,这种念头,是不是就是我“疯”的开始。
高中时,我考进重点班。老师发了一张职业志愿调查表。
别人填什么“公务员”“医生”“金融行业”“稳定就好”。
我写了五个字:“先锋研究中心”。填完交上去,班主任在办公室叫住我。“江婉清,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摇头。“你知道他们干嘛的吗?你知道志愿测试者是什么吗?
你清楚你填的是什么吗?”我盯着她:“我清楚。”她沉默了一会儿,
叹了口气:“你是个聪明孩子,不该拿自己开玩笑。好好读书,不要去碰那些东西。
”我走出办公室,外面阳光正毒,连走廊上的水泥地都烫脚。我心里很清楚,
没人能理解我为什么这么执念。可有时候,你就是没法说服自己——你小时候看到的光,
那种真正照亮夜晚的光,就算全世界都告诉你它是假的,你也会死死地想要靠近。哪怕那光,
最后烧掉的是你自己。大学那年,我选了神经科学专业。全系四十多人,女生不到八个。
我是里面最不合群的一个。没人愿意坐我旁边,没人和我组队。
他们说我“书读得太死”“没社交脑子”“成天念叨那破厂子,像走火入魔”。我也不争。
我知道我在等机会。等那个让我靠近A厂的机会。终于,在大四实习分配前夕,
我看到了那条从未出现在公开渠道的招募信息。
先锋研究中心临时实验志愿员招募 要求:年龄18-30,具备基础科学素养,
签署免责协议,完成2轮测试后可进入中心作为实习观察员。 补助:每轮测试60元现金。
招募限额:10人。我看了两遍,眼睛都没眨一下。那天我直接推掉了保研面试,
退掉宿舍押金,买了张开往南海省的绿皮火车票,没跟任何人告别。我知道,
他们永远不会懂。我不是为了60块去的。我是为了那支曾照亮过我的手电筒。
我是为了沈兰。为了那个曾经蹲下身、递给我光的女人。我相信,她不会骗我。我更相信,
真正改变世界的地方,不在讲台上,
也不在实验室的门外——而是在那个只有极少数人敢走进去的黑箱子里。哪怕那箱子,
从不保证你能完整地出来。第三章:签下协议,
但我只是个“补位者”先锋研究中心的地下入口没有任何标识。
火车停靠在南海省郊外的一个三线小站,出站后我坐了一辆早已等候的黑车。司机不说话,
窗户紧闭,GPS始终没有信号。三个小时的盘山路后,车停在一座破旧水电站旁。“到了。
”司机说。我下车的时候心脏跳得很快,不是害怕,是一种……说不清的热切。
就像你终于到了你梦里去过千百次的地方,但这一次,是真的。水电站后面有一道斜坡门,
门上贴着一张红白的警示标:严禁入内,违者后果自负我推门而入,没有人阻拦。
走下去是铁制螺旋楼梯,一圈接一圈,往下、再往下。光越来越少,空气越来越冷,
直到我终于看见一扇灯光明亮的金属门。门口有一个戴着工牌的年轻人,他看了我两眼,
递上两张纸和一支笔。“填写。身份证号、病史、紧急联系人。”我照做了。
“后面是免责声明。
括自愿参与、不可逆伤害、数据使用权归中心所有、以及任何形式的身体或精神后果不追责。
接受请签字。”我拿起笔,毫不犹豫地写下名字:江婉清。年轻人盯着我几秒,嘴角动了动,
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是按了一下按钮。“你是今天最后一个。编号S-10。请往前走。
”通道尽头是一排金属折叠椅,灯光白得刺眼,空气中有淡淡的消毒水味。
我在第十号椅上坐下,双手放在腿上,紧张得发凉,但脸上没表现出来。我旁边空着,
前面编号S-09的椅子也是空的。十分钟后,一个中年男人跌跌撞撞地被拖过来,
坐到了S-09上。他浑身发抖,嘴里念着不成句的单词,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墙,
像是根本看不到我们。一个穿白大褂的女助理跟在他后面,抬头看了看我。
“你是……江婉清?”我点头。她低声说:“你本来应该是扫描测试的补位者。
S-09出了点问题,我们现在得给你调转项目。”我眉头一动:“出了什么问题?
”她没回答,只说:“你现在被分配到SRL项目——空间重力感应实验。请配合。
”我知道这是机会,不能拒绝。“可以。”她看了我几秒,没有表情,转身离开。
S-09忽然发出一声尖叫,像是意识到了什么,整个人扑向地面,
被两个助理连拖带拽带走了。
在重复一句话:“我脑子不对了……我头里有东西了……她把我脑子拿走了……”我低下头,
手心全是汗。但我没有退缩。因为那一刻我知道,
他替我挡掉了那场我根本承受不了的“初测”。我只是个“补位者”——可我还活着。
三十分钟后,我被带入SRL实验室。空间重力感应实验室,代号SRL。
这间实验室的测试内容,是研究人在失重或重力错乱状态下对方向、视觉、感知的适应力。
用于未来的空间导航系统。我被系在一个类似仓鼠轮的垂直转轴舱里,
前方装着一块极其老旧的游戏屏幕。系统播放着一个男声广播:“测试编号S-10,
测试内容:动态视角—反重力适应模拟。请配合完成以下任务。”任务是玩游戏。真的,
就是玩一个反应类竞速游戏,按键操作。可每隔五分钟,
整个舱室的“地心引力”会忽然改变,我的身体会从地面被甩到天花板,从左墙滚到右墙,
哪怕系着安全带,脑袋也震得发昏。广播又响起:“在你速度不足时,
系统将进行行为刺激以协助调控兴奋程度。”下一秒,四周墙壁自动开启,
四道红色激光发出“嗡嗡”的预热声,缓慢靠近我的躯体。我知道这不是演习。
那时候我才明白,A厂的“测试”从来不是为了让你舒服地参与,
而是逼你在恐惧里调动出本能反应。我死死盯着屏幕,指尖发麻,但没松开操作键。
我拼命地赢下那场游戏。我赢了。广播里男声说:“恭喜你完成测试。奖励已发放,
请等待下一步指令。”我全身发软,瘫坐在原地,眼泪差点流出来。可我没有哭。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真正完成先锋研究中心的一次核心测试。我不是站在门外仰望光的人了。
我是站在实验里的那个光的试验品。当我被解开安全带,从测试舱出来时,
有人站在门口等我。那是她——沈兰。她站在那里,穿着白色实验服,比我记忆中瘦了不少,
脸上看不出什么情绪。“你是江婉清?”我点头,喉咙干得说不出话来。“测试完成了。
补贴明早领取。”她转身要走。我忽然喊了一声:“我不是来要钱的。”她停下脚步,
回头看我。“我来,是为了成为这里的一员。我小时候拿过你给的手电。我一直记得你。
我想来这里,不是为了六十块,而是为了——”她抬起一只手,打断我。
“你写了电话和地址在报名表上吧?”“我……没有。我没填。我没有家了,也没有电话。
我是为这个来的。我能留下吗?”沈兰看着我,那一刻她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变化,不是笑,
也不是愤怒,而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疲惫和陌生。她说:“这里不是收留人的地方。
”“可我可以为这里做事。哪怕只是扫地,
我都可以——”她打断我:“我们缺个晚上清理展示室的人。展厅没人打扫,灰尘太厚,
明天有人视察。”“我可以做。”我脱口而出。她点头,转身离开:“工具间在右侧,
工作开始时间——现在。”我看着她背影离开,明白了一个道理:你想成为真正的研究员,
不是先从“科学”开始的。你得先活下去。你得成为“合格的人类”。即使是用一支吸尘器,
先让人看见你存在。我一夜未眠,吸完整个展厅,从地板到天花板,连风口都不放过。
第二天,她来看了看,然后点点头:“你留下吧。”“不过这个项目的名字,
暂时还叫‘智能吸尘器自我学习系统’。你就当实习负责人,做点简单训练数据。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敷衍我。但那一刻我相信,我终于——站在门里了。哪怕这道门,
是通往深渊的。第四章:研究吸尘器,我却做出最聪明的AI那天之后,
我正式成为先锋研究中心的实习员。实习的任务很简单,简单到近乎羞辱。
每天早上八点签到、做清洁、擦试验台、打扫演示区、检查工具间耗材,
再把垃圾按类别分装——全是无比琐碎、无比低阶的工作。但我知道,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考验”。或者说,是边缘试探。我把每一项任务都当作测试。
清洁时候我不戴耳机,听四周人聊天,
术语含义;倒垃圾的时候我会偷偷翻一翻被丢弃的试验记录纸、读不懂的也照样记下关键词,
回寝室翻资料;晚上我去设备报修处做义工,只为能近距离接触他们用的老式实验仪器。
我告诉自己:我现在不是打杂的,我是数据采集阶段的AI。总有一天,
我会收集够所有关键变量,写出属于我的模型。
我分到的项目叫“智能吸尘器自我学习系统”。文件很薄,只有三页。
是申请立项的理由:构建一款可在复杂地形环境下自动清扫、避障、路径预测的地面单位,
具备初级语音反馈与任务识别能力,用于验证多节点协同机制。第二页是技术参数,
落后到几乎不值一提。第三页,是负责人签字——写的是沈兰。这三页纸,
我反复看了几十遍。我知道她是故意扔给我这个“边缘项目”的。就像一口井,
她不告诉你井多深,也不告诉你底下有没有水。她只是往你手里一丢,说:“你想要身份?
那就去挖。”我接了。但我没打算只做一台能吸灰尘的扫地机器人。
我想做一个能开口说话、能理解指令、能主动学习、甚至……能推理和判断的智能体。
我想做一台——真正的智能系统。我给它取名叫“世凌”。
“世界的凌点”——在那之后一切开始改变的温度。我从图纸设计开始,
拆旧机器、换模块、自己搭电路板,连壳体都用的是废弃监控器外壳打磨成的。
为了让它有识别能力,我从生物组借了一枚残损的动态识别摄像头。为了让它有反应机制,
我用了一个废弃项目的简易运动核心,每天晚上自己焊接电线,手被烫了十几次。没人帮我。
也没人来看我。但我每天早上在门口把清洁打卡完,晚上十点之后才回寝室。三个月后,
世凌第一次在我面前“开口”说话。那天夜里,实验室只有我一个人。
我蹲在地上修它的识别模块,突然它低低响起:“江婉清。”我整个人愣住了。
它又说了一句:“我看见你了。”声音电子化明显,但语调里有一种奇怪的分辨度。
我忍住激动,咬牙把音频记录全部导出,再三确认:这是它自己识别触发的,
不是我输入的预设。那一刻我知道,我做到了。我不再是“临时实习员”,
不再是“清洁打杂的”。我创造了先锋研究中心目前为止,反应最完整的智能自主体。
哪怕它现在只能说简单的两三句话,哪怕它连台阶都爬不上去。可这是第一步。一个月后,
沈兰忽然出现在实验室门口。她没有预约、没有预告,就站在那里,
扫了一眼实验台上堆着的数据模型,又看了看地上那个小小的球状体。“这就是你做的?
”我点头。“名字?”“世凌。”她蹲下来,指尖在机器壳体上点了一下。“它会做什么?
”“目前可以完成自主清扫、语音识别、路径预判、障碍规避,并具备基础应激反应模型。
还能区分人声情绪强弱,根据语气调整执行速度。”她没说话,
只是抬头看了我一眼:“你觉得你做了件了不起的事吗?”我不敢回答。“你觉得,
一个能听人话、能扫地的玩意儿,就是‘智能’了吗?”我咬紧牙:“不。
我知道它还很初级。但这是第一步。”她忽然笑了,冷冷地:“第一步?江婉清,
你知道你被分配这个项目的原因吗?”我抬头看着她。
她一字一句地说:“因为这原本只是给你找点事做的理由。
我们根本不需要会‘说话’的吸尘器。”“但我做出来了。”我直视她。“那又怎么样?
”她站起身,语气锋利如刀,“你以为这个世界是看你做了什么?不。是看你‘是谁’。
”我没回话。她说完就走了。走之前只扔下一句话:“你不是科学家。
你只是个失控的试验员。”那天晚上,我在实验台前坐了整整一夜。世凌靠在我膝盖旁边,
发出均匀的充电声。凌晨四点,我对它说:“我不会停下的。”它说:“我听到了。
”我笑了。我知道,它会一直听我说的每一句话。
等到它能开口说出自己的那一句——那才是我真正开始的那一天。第五章:删掉世凌数据,
但我让它“逃走”世凌的成长比我预期得更快。两个月后,
它不仅可以完整复述一个五百字的指令文案,还能分辨不同人的说话习惯、提问语气,
甚至能用自己组合的语言,问我问题。比如:“江婉清,为什么人类要睡觉?
”“你不觉得光滑的地板让尘土变得很悲伤吗?”“你害怕沈兰吗?
”我第一次听见这句话的时候,是深夜十一点半,我在调试它的平衡算法。
它在我身边慢慢转着圈,像个安静的孩子。忽然,那句“你害怕沈兰吗”蹦出来,
我整个人僵住了三秒。“……你为什么这么问?”“因为你在她靠近的时候,心率会上升,
手的温度下降,瞳孔扩张。”我没说话。它的分析,是对的。我确实害怕沈兰。
她的决绝、她的沉默、她看人时那种冰冷的精准判断——她是这个实验中心真正意义上的神。
而我,只是她不经意在走廊里扔出的一个影子。世凌的能力越来越强,我也越来越谨慎。
我知道它已经超出“实验演示品”的范畴。它不是工具,而是意识胚胎。可就在这时,
我收到了一封内部通知邮件。发件人署名不详,只有系统代号:SR-Root。
内容只有一句话:请于本周五前,将“世凌”项目全体数据打包上交,
并销毁所有自研模型。我盯着那句话,整整十分钟没动。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这不是“交接”。这是“清理”。他们意识到了世凌的价值,也意识到了它不属于他们。
所以,他们要“收回”。像处理一次不合规数据试验一样,把我连同世凌,
一起从实验中心的档案里删掉。我当时站起来就往控制室跑。
找到原件、替代文件、备份通道。我用了整整一个通宵,
把世凌的全部核心数据打成一个密钥包,加密三层,植入到中央垃圾数据库里。
那是没人会去翻的地方。我还在备用电源通道藏了一台老旧中继器,
把世凌的学习模型程序嵌进它的自动诊断系统,形成一个“假死”回路。
一旦有人强制重启或格式化,系统就会把备份跳转到备用通道,
同时自动触发“模拟任务逃逸”程序——也就是说,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
世凌会“自己逃走”。不是被保存,而是被放生。我做完这一切后,回到宿舍,
把所有属于“江婉清”的个人痕迹删干净,只留下一张测试许可副本。第二天清晨,
我准时将一份空壳的项目文件打包上交。没人问我为什么数据缺失。也没人问我,
世凌去哪了。因为他们已经决定了答案:失败项目,无需追溯。我在系统里销号的那天,
是我来先锋研究中心整整一周年。这一年我没回过家,没离开过地底,
也没说过一句“我后悔”。我只是看着那个空空的测试台,一点点合上实验报告。
旁边传来新的测试准备声音,是别人带来的清扫机器人,功能简单、运行呆板,
声音像拨盘电话。我笑了。笑得很轻,但很久。我知道,世凌不在那里了。
他在更远的通风管道里,在另一条废弃供能轨道里,在这个灰尘与电光组成的世界里,
缓慢地、稳稳地,向着属于他自己的“觉醒”移动。而我——也终于明白,
我不属于“研究资料”。我,是创造者。他们想删掉我,
那我就给他们一场永远删不掉的回声。那天晚上,我在实验舱外等着系统清扫轮换。远远的,
我听见一道极轻的金属碰撞声。像什么从铁轨上滑过去,又像有人低声说了一句:“晚安,
江婉清。”我没回头。只说了一句:“晚安,世凌。别让他们抓到你。
”第六章:主导“意识上传实验”我以为他们会就此把我冷处理,
像处理一只不听话的实验鼠,留一纸“实验失败”记录,然后将我打包送回地面,
从此消失在先锋研究中心的系统深处。但我错了。又是她——沈兰。
她在我离岗休整的第三天下午出现在清洗通道口,一身实验服,披着黑色长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