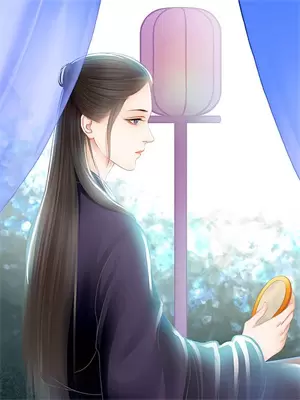北疆有个代代相传的禁忌:暴风雪中若听见女子呜咽,切莫回头张望。
那是一位身着绀青色和服、怀抱冰棱镜的雪女,她会在你回头瞬间,
用镜光照出你心底最悔恨的往事。而后,寒气便会顺着你的记忆脉络冻结全身,
将你化作一尊晶莹剔透的冰雕,永世矗立于风雪之中。据说,
她是在寻找千年前那位背弃诺言、害她冻毙荒野的情郎。---北疆的冬天,不是季节,
是一种刑罚。那风,不是吹过来的,是千万把看不见的冰刀子,贴着地皮刮过来,
能剐掉人一层皮,再钻进骨头缝里,把骨髓都冻成冰碴子。天地间就剩两种颜色,
头顶是铅块一样沉、低得快要压到眉毛的灰白天,脚下是白茫茫一片死寂的雪原,
一直铺到世界尽头。在这片能把活人生生冻成硬邦邦的“冻梆子”的绝地里,
却有个比严寒更刺骨的传说,代代相传,像雪原底下埋着的陈年冰棱,碰一下,就透心凉。
老人们围着哔剥作响的牛粪火堆,压低了声音告诫后生:赶夜路,
遇上遮天蔽日的“白毛风”暴风雪,若是风里夹杂进一丝半缕女人的呜咽声,幽幽怨怨,
像是从地底钻出来的,那你可得把魂儿拴牢了,千万,千万,莫要回头张望。那呜咽的,
不是山精野怪,是“雪女绀青”。她呀,
传说穿着一身旧得发白、却依然能辨出原本是绀青色的东瀛和服,
在那能把人瞬间冻僵的风雪里,衣袂飘飘,竟不沾半片雪花。怀里总抱着一面镜子,
不是寻常铜镜玻璃镜,是北疆万丈冰崖下才能采得的千年寒冰,打磨得光滑如镜,
唤作“冰棱镜”。你若按捺不住那点该死的好奇心,或是被那哭声勾走了魂,
回头那么一瞥——镜光就会亮起,不刺眼,却冰冷彻骨,
直直照进你心窝子里最见不得光、最悔不当初的那一处。可能是你失手打翻药碗,
害死了卧病在床的老母;可能是你为几块银元,出卖了过命的兄弟;可能是你贪恋野花,
抛下了发妻稚子……总之,是你这辈子最想忘、却偏偏忘不掉的腌臜事。寒气,
便会顺着这记忆的脉络,像活物一样,悄无声息地爬遍你的全身。先是手脚麻木,
再是血液凝滞,最后连呼出的最后一口气,都在嘴边冻成了冰溜子。你就那么站着,
眼睁睁看着自己从里到外变成一尊晶莹剔透的冰雕,眉眼惊恐,姿态凝固在回头的那一瞬,
成了这无边雪原里又一具沉默的装饰。你的魂儿呢?据说就被封在那冰壳子里,日日夜夜,
受那风刀霜剑,永世不得超生。至于雪女绀青为何如此残忍?老故事里絮絮叨叨地说,
她是在找一个人。一个千年前,在这片同样寒冷的土地上,对她许下海誓山盟,
却最终背弃诺言,害她孤身一人,冻毙荒野的负心郎。千年了,
她抱着那面能照见人心污秽的冰棱镜,一遍遍拷问每一个在风雪中回头的过客,
盼着能照出那张刻骨铭心的脸,又或许,只是想看看,这世间的男子,是否都如他一般,
心比冰寒。这传说,在北疆的冬夜里,比任何狼嚎熊啸都更能让牧人早早栓紧帐篷的门帘,
让行商宁可绕上三天的远路,也绝不轻易在暴风雪里赶夜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啊。
这一年,北疆的冬天来得格外早,也格外酷烈。刚进腊月,
一场几十年不遇的“白毛风”就毫无征兆地扑了过来,刮得天地失色,日月无光。恰巧,
有一支小小的驮队,被困在了风口浪尖上。领头的叫巴特尔,是个四十来岁的北疆汉子,
身材魁梧得像头人立起来的棕熊,脸膛被风沙和烈酒染成了紫红色,
一把络腮胡子纠结在一起,能藏下半斤沙子。他在这条连接关内关外的古商道上跑了十几年,
经验老道,可面对这场风魔,也心里直打鼓。驮队里除了他,
还有他刚满十六岁、第一次跟着跑远道的儿子其格,以及一个搭伙的关内皮货商,姓陈,
瘦瘦小小,话不多,眼神里总带着点商贾特有的精明和警惕。狂风卷着雪粒子,
砸在厚厚的皮袄上噗噗作响,像是有无数小鬼在敲打。天色迅速暗沉下来,
几步之外就看不清人影,只能靠拴在腰间的绳子勉强保持着联系。驼铃早就被冻哑了,
平日里温顺的骆驼此刻也焦躁不安地喷着响鼻,蹄子深深陷进雪窝里,举步维艰。
“阿布父亲!风太大了!找个地方避避吧!”其格年轻,体力好,但也被这阵势吓住了,
扯着嗓子在风里喊,声音抖得厉害。巴特尔眯着眼,努力辨认着方向。
他记得这附近应该有一处废弃的烽火台,石头垒的,能挡挡风。“再撑一会儿!
前面有落脚地!”他吼着回应,心里却也没底,那烽火台荒废多年,也不知被雪埋了多深。
陈掌柜紧紧捂着装账本和银票的皮囊,脸色比雪还白,嘴里不住念叨:“真是流年不利,
流年不利啊……”就在这时,一阵异样的声音,穿透了狂风的怒吼,钻进了三人的耳朵。
呜……呜呜……不是风声的尖啸,那声音更细,更绵长,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哀怨,
像是有个女人在极远的地方哭泣,又仿佛就在你背后脖颈子边上吹气。其格最先听见,
年轻人耳朵灵,他猛地一僵,扯了扯腰间的绳子:“阿布!你……你们听见没?
”巴特尔心里“咯噔”一下,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比这天气更冷。他当然听见了。
那声音……跟传说里的一模一样!他强作镇定,头也不敢回,低声呵斥:“闭嘴!捂上耳朵!
赶紧走!什么也没听见!”陈掌柜显然也听到了,他浑身一哆嗦,下意识地就想扭头往后看,
被巴特尔一把按住肩膀:“不想变冰梆子就别回头!”呜咽声时断时续,忽左忽右,
像是在戏弄他们。它有时像年轻的少女在啜泣,有时又像饱经风霜的妇人在哀叹,
在这混沌的风雪世界里,显得格外瘆人。骆驼们更加焦躁,甚至试图挣脱缰绳。
其格的脸吓白了,牙齿咯咯打颤,关于雪女绀青的种种恐怖描述瞬间塞满了他的脑袋。
陈掌柜则眼神闪烁,那哭声似乎勾起了他什么心事,脸上血色褪尽,
搭在皮囊上的手抖得厉害。巴特尔心知不妙,只能拼命催促:“快!快走!烽火台就在前面!
”他现在只盼着那传说中的鬼地方只是个传说。然而,命运似乎偏要跟他们开个玩笑。
就在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好不容易蹭到一处背风的石坡下,
隐约看到前方似乎有段残破石墙轮廓时,其格脚下一滑,“哎呦”一声摔倒在地。这一摔,
系在他腰间的绳子猛地一拽,连带着心神不宁的陈掌柜也是一个趔趄。
陈掌柜本就处在极度惊恐中,这一下彻底失去了平衡,慌乱中,
他下意识地扭头想抓住点什么——他的目光,越过白茫茫的风雪,
似乎瞥见了一道模糊的、绀青色的影子,静静地立在十几步外。还有……一面镜子般的寒光,
一闪而过。“啊——!”陈掌柜发出半声短促的尖叫,就像被人掐住了脖子,
后半截硬生生憋了回去。他整个人僵在原地,保持着扭头的姿势,眼睛瞪得溜圆,
瞳孔里映出的不再是风雪,而是某种无法形容的、源自内心的极致恐惧。
巴特尔暗道一声“完了!”,也顾不得许多,猛扑过去,想将陈掌柜按倒,挡住他的视线。
可是已经晚了。陈掌柜的身体,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失去了血色,变得青白。
他的皮肤表面,开始凝结出细密的白色霜花,霜花飞快增厚,变成透明的冰层,
从他的脸颊、脖颈向下蔓延。他张着嘴,似乎想呼喊,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只有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像是气管被冻住的怪响。不过短短几个呼吸间,
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在巴特尔父子眼前,变成了一尊栩栩如生、满脸惊骇的冰雕!
连他脸上那最后一丝惊恐的表情,都凝固得清清楚楚。冰雕保持着扭头的姿势,立在风雪中,
怀里的皮囊也冻成了冰块。其格吓得瘫软在地,屎尿齐流。巴特尔也是浑身冰凉,手脚发软,
他死死拉住儿子,不敢再看那尊冰雕,也不敢回头,只能凭着最后一点力气,
拖着几乎傻掉的其格,连滚带爬地扑向不远处那段残破的石墙。风雪依旧。那呜咽声,
在制造了一尊新的冰雕后,似乎满意了,渐渐低了下去,最终消失在狂风的呼啸里。
巴特尔父子缩在烽火台半塌的墙角,用冻僵的手扒开积雪,紧紧挤在一起,
靠着彼此那点微弱的体温和巨大的恐惧支撑,熬过了这个毕生难忘的恐怖夜晚。天亮了,
风停了。雪原上一片死寂,阳光照在雪地上,反射出刺眼的白光。那尊属于陈掌柜的冰雕,
在晨曦中闪烁着诡异的光芒,提醒着昨夜发生的一切并非噩梦。巴特尔带着精神恍惚的儿子,
不敢久留,草草掩埋了陈掌柜的冰雕虽然知道这毫无意义,继续踏上归途。
只是从此以后,巴特尔的鬓角多了许多白发,其格也再不是那个天真烂漫的少年。
北疆的雪原上,关于雪女绀青的传说,因为又多了一具冰雕佐证,而变得更加真实,
更加令人胆寒。然而,传说,才刚刚开始它的低语。陈掌柜的冰雕,
或许并不仅仅是又一个不幸的遇害者。他临死前那极致的恐惧,他眼神里映出的东西,
以及雪女绀青为何偏偏在此时此地现身……千年的寻找,似乎并未停止,反而,
因为某些不为人知的牵连,掀开了新的篇章。那面冰棱镜照见的,真的只是负心郎的魂魄吗?
还是说,这冰封的诅咒之下,埋藏着更深的、关于背叛、遗忘与救赎的秘密?
巴特尔父子带着一身冻伤和更深的心理创伤,侥幸逃回了聚居的屯子。
陈掌柜化作冰雕的惨状,像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牢牢刻在父子俩的心头,
尤其是年轻的其格,夜里时常惊厥,呓语中尽是风雪与绀青色的鬼影。这桩惨事,
经由其他往来商队的口耳相传,迅速发酵,雪女绀青的恐怖传说,
如同这场几十年不遇的严寒一样,迅速笼罩了整个北疆。人们谈及那片通往关外的古商道时,
眼神里都带着难以掩饰的恐惧,入冬后,更是几乎绝了人行。然而,总有不信邪的,
或是被某种宿命牵引而不自知的人。就在巴特尔父子逃回后约莫半个月,
一支小小的、与北疆粗犷风格格格不入的队伍,顶着渐弱的风雪,艰难地抵达了屯子。
队伍只有三人,领头的是个三十岁出头的男子,名叫铃木修介,穿着厚实的西洋式探险服,
面容斯文,却带着一股执拗的书卷气。他是来自东瀛的民俗学者,
专程为考察北亚冰雪地带的神话传说而来。跟随着他的,
是一名沉默寡言、皮肤黝黑的当地向导阿木尔,
以及一个负责物资和联络的年轻中国助手小周。铃木修介的到来,
在屯子里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他出手阔绰,租下了屯子里最好的一间空屋,
又四处打听关于雪山、冰湖、特别是“雪女”的传说。
当巴特尔父子遭遇雪女绀青的故事传入他耳中时,这个年轻的学者非但没有流露出惧色,
反而显得异常兴奋,那双藏在圆框眼镜后的眼睛,闪烁着近乎狂热的光芒。
“绀青色和服……冰棱镜……寻找负心郎……”铃木修介在临时充作书房的屋子里,
反复念叨着这些关键词,面前铺着泛黄的古籍复印件和北疆的简陋地图。
他的手指在地图上巴特尔遇险的那片区域重重划过,“没错,一定有关联!
家族记载里的‘青女’,传说飘洋过海去了北方的雪国……时间、特征,都对得上!
”小周在一旁整理着行李,看着自家先生激动的样子,忍不住泼冷水:“先生,
那毕竟只是个传说,而且那么危险。巴特尔他们差点就回不来了。咱们还是稳妥点,
在屯子附近收集点资料就好。”阿木尔则蹲在火塘边,默默地擦拭着他的猎刀,闻言抬起头,
用生硬的汉语说:“铃木先生,白毛风里的东西,不能碰。那是山神爷的领域,惹怒了,
要遭殃的。”他的眼神里带着牧民特有的、对自然力量的敬畏。铃木修介却摇了摇头,
语气坚定:“不,阿木尔,小周,你们不明白。这不仅仅是一个传说,它可能关乎我的家族,
关乎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他深吸一口气,从随身携带的一个紫檀木小匣里,
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件东西。那是一枚已经褪色、但依然能看出原本是绀青色的丝绸碎片,
边缘绣着精细的、类似冰晶纹路的残破图案。碎片被仔细地裱在一张硬纸上,
看得出年代极为久远。“这是我家代代相传的,‘青女’离去时留下的唯一信物。
”铃木修介的声音低沉下来,带着一种复杂的情感,“家族记载,千年前,
一位名叫‘青’的先祖,爱上了一位来自北方大陆的使节或商人。她不顾家族反对,
随他远赴这片苦寒之地,却最终被抛弃,客死异乡,怨念不散,化作了雪女。
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个美化过的悲剧故事,
直到我看到了关于北疆雪女的记载……”他指着那块绀青色碎片:“这颜色,这纹样,
和传说中雪女绀青的和服描述,何其相似!还有那面镜子……家族记载里,‘青’最爱惜的,
就是一面来自唐国的水银镜……”小周和阿木尔面面相觑,
他们无法理解铃木修介这种近乎偏执的考据热情,更无法将眼前这个文质彬彬的学者,
与那个风雪中索命的恐怖雪女联系起来。“可是先生,就算她真是您的先祖,
那也是一千年前的事情了!她现在……她现在是个杀人的鬼怪啊!”小周试图做最后的劝阻。
铃木修介却像是下定了决心:“正因为如此,我才更要找到她。
或许……或许我能化解她的怨气,让她得以安息。这也是我此行的最终目的。”他的眼神中,
除了学术的探究,似乎还隐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赎罪感?
或是家族后代对先祖悲剧命运的一种责任?无论小周和阿木尔如何劝说,
铃木修介都铁了心要前往巴特尔遭遇雪女的那片区域进行实地考察。他出重金,
希望阿木尔能带路。阿木尔起初坚决拒绝,但铃木修介不仅加价,还承诺只在区域外围勘察,
绝不深入险地,并且保证一旦天气有变,立刻撤回。加之屯子里一些老人也在议论,
说雪女绀青似乎只在特定的、极大的暴风雪中才会出现,平时或许并无大碍。
阿木尔权衡再三,想到家中急需用钱,最终咬牙答应了下来。几天后,天气暂时晴好,
铃木修介、小周在阿木尔的带领下,带着足够的补给和考察设备,骑着马,
向着那片被死亡阴影笼罩的古商道进发了。越靠近那片区域,周围的景色越发荒凉。
积雪覆盖了一切生命的痕迹,只有枯死的灌木和嶙峋的怪石,像墓碑一样点缀在雪原上。
空气冷得像是凝固了,连马蹄踏雪的声音都显得异常空洞。阿木尔变得格外警惕,
不时停下来观察风向和云层,嘴里用蒙语念叨着祈福的经文。铃木修介却显得异常活跃,
他不停地拍照、记录,用仪器测量着什么,
尤其对任何可能与“镜面”或“反光”有关的东西感兴趣——冰封的湖面、光滑的岩石,
甚至是一些特殊的冰晶结构。他怀里紧紧揣着那个装有绀青色碎木匣,仿佛那是他的护身符。
小周则提心吊胆,总觉得四周白茫茫的雪地里,随时会冒出那道绀青色的鬼影。
他们找到了巴特尔描述的那处废弃烽火台。石墙残破,在积雪中半埋半露,更添几分凄凉。
阿木尔指着不远处一个微微凸起的雪堆,
声音低沉:“那里……就是陈掌柜……”雪堆已经看不出人形,被新雪覆盖,
但依然能感受到一种不祥的气息。铃木修介走到雪堆前,沉默地站了片刻,
然后竟拿出罗盘和一些奇怪的探测仪器,在周围忙碌起来。小周和阿木尔远远看着,
心里直发毛。“先生,差不多了吧?天色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小周忍不住催促。
铃木修介却像是发现了什么,蹲下身,用手套拂开一片积雪,露出底下颜色略深的冻土。
……有微弱的异常波动……和家族记载中提到的‘灵镜’扰动的描述很像……”他喃喃自语,
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里。就在这时,一直警惕观察着天空的阿木尔脸色骤变:“不好!
起风了!云头压下来了!要变天!快走!”只见天边,原本还算明亮的天空,
迅速被铅灰色的乌云吞噬,狂风骤起,卷起地上的积雪,能见度急剧下降。
正是北疆最可怕的“白毛风”的前兆!铃木修介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惊醒,
他慌忙收起仪器:“快!上马!回撤!”三人翻身上马,朝着来路狂奔。然而,
风雪来得太快、太猛了。不过片刻功夫,天地间就变成了一片混沌的白色,狂风怒吼,
雪片横飞,几乎让人睁不开眼。马匹受惊,嘶鸣着不肯前行。他们迷路了。
在这片几乎一模一样的雪原上,失去了所有参照物。“找个地方避风!不然我们都得冻死!
”阿木尔在风声中大吼,凭借着多年在野外生存的经验,勉强辨识着方向,
带领两人挣扎着向一处看起来像是背风坡的地方挪去。风雪越来越大,温度急剧下降。
就在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几乎绝望的时候,小周突然指着侧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