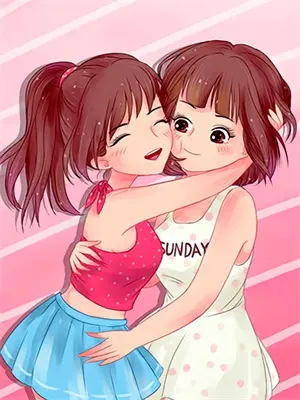
一杯毒酒穿肠过,我,大景朝废太子萧景琰,死不瞑目。弑君篡位?毒杀兄弟?
这泼天的罪名,是我那“仁德”的皇弟和“贤淑”的太子妃亲手为我罗织。再睁眼,
我竟回到被废前三月。前世,我优柔寡断,满口仁义,却落得身败名裂、妻离子散。这一世,
去他的兄友弟恭,去他的君臣大义!既然你们说我是魔,那我便魔临天下。所有负我之人,
且看好了,这盘死局,我如何一步步,杀回金銮殿!第一章:惊魂头痛欲裂,
像是有人用钝器一下下砸着我的颅骨,喉咙里火烧火燎,
残留着某种甜腻又辛辣的液体灼烧感。是了,鸩酒。皇家特供,入口柔和,穿肠烂肚。
我猛地睁开眼,刺目的光线让我一阵眩晕。映入眼帘的,是熟悉的明黄帐顶,
蟠龙绣纹张牙舞爪。这里是……东宫,我的寝殿?我还没死?
还是说……地府也流行这套皇家规制?我挣扎着坐起身,环顾四周。殿内陈设一如往昔,
紫金香炉里袅袅吐着熟悉的龙涎香,窗外夜色深沉,淅淅沥沥的雨声敲打着琉璃瓦。不对。
我被废黜后,软禁于冷宫偏殿,饮下毒酒时,分明是个燥热的夏夜,何来雨水?“殿下,
您醒了?”一个带着惊喜的、略显阴柔的声音在帐外响起。我浑身一僵。
这个声音……是曹谨言!那个在我被废后,依旧对我不离不弃,
最后随我一同被赐死的老太监!我掀开帐幔,
看到曹谨言那张布满皱纹、此刻却写满担忧的脸。
他不是……已经在我之前……“现在是什么时辰?何年何月?”我的声音沙哑得厉害,
带着自己都未察觉的颤抖。曹谨言虽疑惑,却依旧恭敬回答:“回殿下,
现在是景和二十三年,四月初三,亥时三刻。您方才批阅奏折时晕倒了,太医来看过,
说是劳累过度,开了安神的方子。”景和二十三年……四月初三!我如遭雷击,心脏狂跳,
几乎要撞碎胸骨!我竟然……回来了?回到了我被废黜的三个多月前!前世的一幕幕,
如同潮水般涌入脑海,带着刻骨的恨意与绝望。我最信任的皇弟萧景恒,
在我背后捅了最狠的一刀,联合我最爱的太子妃苏浅雪,伪造我勾结边将、意图逼宫的铁证。
那个一向对我忌惮有加的父皇,甚至没有给我申辩的机会,一道圣旨,废我太子之位,
打入冷宫,最后赐下鸩酒。我记得萧景恒端着毒酒走进来时,
那副悲天悯人又掩不住得意的嘴脸:“皇兄,您安心去吧。这万里江山,
弟弟会替你打理好的。”我记得苏浅雪依偎在萧景恒身旁,
用我最迷恋的温柔语调说:“殿下,成王败寇,莫要怨怼。要怪,就怪你太过天真,这龙椅,
从来不是给仁君坐的。”仁君?天真?哈哈哈哈哈!好一个仁君!好一个天真!
我前世就是太信奉所谓的仁义道德,太过顾念兄弟之情、夫妻之义,
才会被这对狗男女玩弄于股掌之上,最终输掉一切,连性命都保不住!
冰冷的杀意在我眼底凝结,如同万年不化的寒冰。曹谨言似乎被我一瞬间散发出的戾气所慑,
小心翼翼地问:“殿下……您……您还好吗?可要再用一碗安神汤?”我抬眼看向他,
这个前世唯一对我忠心耿耿、陪我赴死的老仆。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翻腾的气血和杀意。
“不必。”我的声音恢复了平静,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冷硬,“谨言,更衣。”“殿下,
夜深了,还下着雨,您要去哪儿?您的身子……”曹谨言满脸担忧。我走到窗边,
推开菱花格窗,冰冷的雨丝随风扑在脸上,带来刺骨的清醒。夜幕深沉,雨幕笼罩下的皇城,
像一头蛰伏的巨兽,散发着危险又诱人的气息。“睡不着,出去走走。
”我望着太极殿的方向,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去听听雨,
也去好好看看……这片即将天翻地覆的江山。”既然老天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那么这一次,我萧景琰,绝不会再重蹈覆辙!所有负我、叛我、害我之人,你们的好日子,
到头了。等着吧。好戏,才刚刚开场。第二章:暗棋雨丝细密,打在青石板上,
溅起细碎的水花。我撑着油纸伞,漫步在东宫寂静的回廊下,曹谨言提着一盏昏黄的灯笼,
默不作声地跟在我身后半步的位置。夜色和雨幕是最好的掩护,也最适合思考。
景和二十三年,四月初三。这个时间点,像烧红的烙铁,烫在我的记忆里。前世,
大约就是十天后,漕运会出一桩不大不小的纰漏,
一批运往江南的贡绸在河道上遭了“水匪”,损失不小。看似意外,
实则是萧景恒手下的人做的手脚,意在打击我当时在户部倚重的一位侍郎。我当时并未深究,
只当作寻常案件处理,轻轻放过,却因此寒了手下人的心,
也让萧景恒试探出了我的“软弱”。这一世,这桩“意外”,
或许能成为我落下的第一颗棋子。“谨言。”我停下脚步,望着廊外被雨水打湿的芭蕉叶。
“老奴在。”曹谨言立刻躬身,灯笼的光晕将他谦卑的身影拉得忽长忽短。“我记得,
你有个干儿子,是在漕运码头上做书记的小吏?”我语气平淡,仿佛随口一问。
曹谨言身子微微一颤,眼中闪过一丝惊疑。他那个干儿子,
不过是码头上千百个小吏中不起眼的一个,连他自个儿都很少提及,殿下日理万机,
如何得知?但他深知宫规,不该问的绝不多问,立刻回道:“殿下明察,确有此事。
那孩子叫小顺子,还算机灵,在码头上做些记录往来船只的杂事。”“嗯。”我微微颔首,
“给他递个话,让他最近警醒些,特别是往来江南的绸缎船队,若有任何异常,
哪怕是捕风捉影的闲话,都记下来,通过你,报与我知。”我没有明说会发生什么,
只是布下一个眼线。小顺子位置低微,反而更容易听到一些上面人听不到的风声。这颗暗棋,
现在埋下,静待发芽即可。曹谨言虽然不解其意,但见我语气郑重,立刻应道:“是,
老奴明白,明日就想办法递话出去。”我点了点头,继续往前走。雨声淅沥,
敲打着我的心绪。光靠一个小吏自然不够,我需要更多的手,更多只忠于我、或者说,
忠于我能给予他们未来的力量。我想起了另一个人,沈墨。一个因言获罪,被贬黜出京,
如今应该在京郊某个穷乡僻壤守着仓库的前任御史。此人性格刚直,不懂变通,
前世因为上书弹劾萧景恒母族侵占民田,被罗织罪名罢官。直到我死,他都未曾屈服。
这是个真正的孤臣,或许,能为我所用。“谨言,还有一事。”我停下脚步,转身看着他,
“明日,你想办法,悄悄去一趟京西的甲字库。”甲字库是存放陈旧物资的仓库,
沈墨如今就在那里担任看守库房的小官,形同流放。曹谨言眼中的惊疑更甚,
但还是垂首听令。“去找一个叫沈墨的库管。不要暴露你的身份,只需观察他,
看他每日做些什么,与什么人来往。若有机会,
试探一下他对如今朝中‘漕运’、‘勋贵’的看法,听听他怎么说。”我不能直接去招揽他,
那样目标太大,容易打草惊蛇。必须先观察,确认他是否还保持着前世的风骨,
再决定如何下手。让曹谨言去,最是稳妥。曹谨言这次沉默了片刻,
才低声道:“殿下……您这是要……?”我看着他眼中掩饰不住的担忧,
知道这位老仆是怕我行差踏错。前世,我就是太过“光明磊落”,才输得一败涂地。
我轻轻笑了一下,笑容里却没有丝毫温度,只有雨夜般的凉意:“谨言,你觉得,一头狼,
在发现周围全是猎人伪装的羊皮时,是该继续吃草,还是该……露出獠牙?
”曹谨言浑身一震,抬头看我,昏黄的灯光下,
他看到的是一双深不见底、再无半分往日温润的眼睛。那里面,是冰冷的杀意和决绝的清醒。
他立刻低下头,声音带着一丝哽咽,却又无比坚定:“老奴……明白了。殿下放心,
老奴知道该怎么做。老奴这条命,早就是殿下的了。”“去吧,小心些,别让任何人察觉。
”我摆了摆手。曹谨言躬身,悄无声息地退入雨幕中,身影很快消失不见。
第三章:金雨雨接连下了三日才放晴。在这三天里,曹谨言依命行事,
带回了关于沈墨的初步消息。“殿下,那沈墨……”曹谨言回禀时,面色有些复杂,
“果真如殿下所料,是个倔强到底的性子。他在甲字库那等清冷之地,
每日竟仍坚持早起诵读,所读皆是圣贤治世之言。与其他库吏攀谈,
言必称漕运积弊、勋戚奢靡,愤世嫉俗,以至于同僚都避而远之,视其为灾星。
”我静静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沈墨还是那个沈墨,一把宁折不弯的剑。
这样的人,无法用名利收买,但现在去招揽,为时过早。“嗯,知道了。”我淡淡应道,
“继续留意即可,暂不必与他接触。”眼下,有更重要、更紧迫的一步棋要先走。
萧景恒为我准备的“大礼”,快要送到了。东宫一切如常,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
我依旧每日按时去文华殿听讲,去户部观政,言行举止与往日那个温良恭俭的太子并无二致。
曹谨言办事利落,不过两日,便通过小顺子有了更确切的消息。夜里,他低声禀报:“殿下,
小顺子说,码头上风声更紧了。那几位被安排押运贡绸船的管事,这几日都称病不出,
家小也似有安排。还有,那几艘标记要出问题的旧船,装载的私货尤其多,
多是江南丝绸商号的货,仓单都攥在几个小商贾手里,他们眼下正为货款周转不灵发愁,
四处想低价脱手仓单套现。”我眼中寒光一闪。果然如此!萧景恒不仅要毁贡品,
还要趁机榨干那些依附于漕运的小商贾,让他们血本无归,真是狠毒又贪婪。而这,
正是我的机会。“我们手头,能动用的银钱,还有多少?”我问道。
曹谨言报出一个数字:“殿下,东宫用度皆有定例,您平日节俭,除去日常开销和人情往来,
能随时支取的……大概还有五千两左右。”五千两。足够了。“你明日出宫,
去找京城‘永兴’票号的掌柜,用不同的化名,开几个隐秘户头,将银子分散存入。
”我吩咐道,“然后,找几个绝对可靠、面孔生疏的代理人,
去接触那些想脱手仓单的小商贾。用比市面更低的价格,
把他们手里那几艘‘问题船’上所有私货的仓单,全部吃进。
”曹谨言倒吸一口凉气:“殿下,这……一旦船沉,这些仓单可就是废纸了!
风险是否……”“没有风险。”我的语气斩钉截铁,“按我说的去做。记住,动作要快,
要分散,不要引起任何注意,尤其不能让人察觉资金来自东宫。”我要做的,
就是在灾难发生前,充当最后一个“接盘”的傻瓜,
用真金白银买下那一堆即将变成废纸的凭证。萧景恒,你恐怕想不到,
会有人抢着跳进你这个坑里吧?事情进展得出奇顺利。在船队出发前最后两天,
几个神秘的买家以“急人所急”的姿态出现,用低至原价三成的价格,
收购了一批“倒霉蛋”商贾手中的仓单。那些商贾庆幸不已,丝毫不知自己躲过了一劫,
更不知收购他们“废纸”的,是即将索命的阎王。十日后,
消息传来:江南贡绸船队于津门附近水道,因“船只老旧,突遇风浪”,数船倾覆,
贡绸损失大半,一同沉没的,还有大量商贾托运的私货。朝野震动,父皇下旨严查。
消息传开,那些损失了货物的商贾如丧考妣,尤其是那些刚刚“幸运”地卖掉了仓单的,
更是后怕不已,纷纷称赞那几位神秘买家是“冤大头”、“活菩萨”。而真正的风暴,
此刻才刚开始酝酿。货沉了,仓单在我手里。
但我要兑付的对象是制造了这场“意外”的幕后黑手本身。我通过曹谨言,
向那几个代理人下达了第二条指令:不必声张,只需通过隐秘的渠道,
首尾的萧景恒门下某个关键人物知道——有一批能指向他们故意破坏、侵吞货值的仓单凭证,
落在了“不明身份”但显然知晓内情的人手里。想要吗?这是阳谋。对方明知道是敲诈,
却不得不吞下这枚苦果。因为如果这些仓单被捅到台面上,再加上有心人追查,
他们伪造意外、贪墨货值的勾当很可能暴露。相比之下,花一笔钱买回“证据”和“平安”,
是最划算的选择。一场无声的交易在暗夜里完成。对方派出的代表,甚至不敢多做讨价还价。
五千两本金购入的“废纸”仓单,换回了整整五万两雪花银,
悄无声息地流入了我在“永兴”票号的各个化名户头。萧景恒在朝堂上故作沉痛,
参劾我那位负责漕运的侍郎失职。我冷眼旁观,未发一言,甚至在父皇征询意见时,
还“大度”地说了几句“天灾难免,当以整顿漕务为重”的场面话。没有人知道,
这场让萧景恒小胜一局、让我的手下折损一员的“意外”,真正的最大赢家,
是我这个看似吃了亏的废太子。我不仅全身而退,还获得了未来行动急需的巨额资金,
更在对手的心脏地带,埋下了一颗恐惧的种子——他们开始意识到,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
正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看着票号送来的密信上那个惊人的数字,我轻轻将信纸凑近烛火。
火苗舔舐着纸张,化作一缕青烟。第一场金雨,已然落下。这雨水,带着血腥味,
也带着权力的甜腥气。而这,仅仅是个开始。第四章:离间五万两雪花银,像一剂强心针,
注入了我原本有些孱弱的脉络。钱是英雄胆,更是阴谋家的血肉。有了它,
许多之前只能停留在脑海里的计划,终于可以缓缓展开。但我比谁都清楚,现在的我,
依旧脆弱。萧景恒在朝中经营多年,党羽遍布,而我这个废太子,看似地位尊崇,
实则如履薄冰,身边不知有多少双眼睛盯着。直接招兵买马是取死之道,眼下最要紧的,
不是在外部扩张势力,而是要从内部,撬动敌人的根基。萧景恒的势力并非铁板一块。
他最大的依仗,除了父皇那点可怜的宠爱,便是以吏部尚书赵文渊为首的那一干文官,
以及他母族——镇北侯府为首的勋贵集团。文官贪权,勋贵贪利,
这本就是最容易滋生裂隙的地方。我的目光,落在了赵文渊的宝贝儿子,赵元昊身上。
此人是京城有名的纨绔,好色贪杯,仗着其父权势横行无忌。前世,
大约就在漕运案风波稍平后,赵元昊在城外别苑强抢民女,失手打死了那女子的老父,
闹出了人命。此事被萧景恒动用权势强行压了下去,赵文渊也因此对萧景恒更加死心塌地。
这一世,这件事,或许可以换个玩法。我不需要阻止悲剧发生,我只需要……让该知道的人,
在合适的时间,以无法掩盖的方式,知道这件事。“谨言。”我轻唤一声。曹谨言应声而入,
姿态比以往更加恭谨。经过“金雨”之事,他对我已不仅是忠诚,
更带着一种近乎迷信的敬畏。“殿下有何吩咐?”“赵尚书家的公子,近日可有什么趣闻?
”我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状似无意地问。曹谨言心领神会,低声道:“回殿下,
那赵元昊,三日后要在城外‘流云别苑’办一场诗酒会,邀请了不少……风雅之士。
”他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鄙夷,所谓风雅之士,不过是些趋炎附势的清客和青楼名妓。
“流云别苑……好地方,清静。”我放下茶杯,目光幽深,
“找两个机灵可靠、面孔陌生的小厮,三日后混进去伺候。不必做别的,
只需在赵公子酒酣耳热、兴致最高的时候,‘不小心’让他听到一个消息。”“请殿下示下。
”“就说,城西豆腐匠张老实的闺女,名叫小娥的,生得极为水灵,堪比天仙,可惜家贫,
明日要被她那嗜赌的父亲卖给城东王屠户做填房了。”我缓缓说道,语气平静无波,“记住,
要说得惋惜,要勾起赵公子的……怜香惜玉之情。”曹谨言眼中闪过一丝了然。
那豆腐匠张老实是个本分人,女儿小娥也确实有几分姿色,但绝无被卖一事。
这是要给赵元昊递上一把作恶的由头!殿下这是要借赵元昊这把蠢刀,
去劈向赵文渊和萧景恒之间的信任基石。“老奴明白。”曹谨言沉声道,“定会安排妥当,
绝不会牵连到殿下分毫。”“嗯。”我点了点头,“还有,事发之后,不必我们的人去告官。
你想办法,让都察院那个新晋的、以耿直著称的御史刘铭,‘偶然’路过流云别苑附近。
再让他,‘偶然’听到那家人的哭诉。”刘铭此人,前世就因为过于耿直,不懂变通,
被萧景恒寻了个由头贬到了蛮荒之地。但此刻,他正是最好用的那把枪。我要借他的口,
将这件事捅到明面上,捅到连萧景恒都无法轻易捂住的程度。曹谨言深吸一口气,
已然看到了即将掀起的风波:“是!”三日后,流云别苑。一切如我所料。酒色之徒赵元昊,
在酒精和美言的刺激下,那点可怜的“侠义心肠”和占有欲被彻底点燃。他带着豪奴恶仆,
直奔城西豆腐坊,不仅要“救”小娥于水火,更要将其据为己有。张老实自然拼命阻拦,
冲突之中,被赵元昊随手一挥,头撞在石磨上,当场气绝。消息传来时,我正在书房练字,
笔下是一个浓墨重彩的“乱”字。“殿下,事成了。”曹谨言低声道,
“刘御史当时正好在附近访友,听闻哭喊声赶去,亲眼目睹了惨状,已连夜写下奏本,
据说……措辞极为激烈,直指赵尚书教子无方、纵子行凶,还暗指背后有更大依仗。
”“很好。”我搁下笔,看着那个仿佛要跃纸而出的“乱”字,“让我们的人,
什么都不要做,静静看着就好。”朝堂之上,风暴骤起。耿直的刘铭果然如一头倔牛,
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将奏本念得声泪俱下,细节详实,字字诛心。赵文渊当场就差点晕过去,
跪地请罪,老泪纵横。萧景恒的脸色难看至极。他必须保赵文渊,这是他的臂膀。
但他若强行袒护,必然惹上一身腥臊,尤其刘铭那句“背后有更大依仗”,
几乎是指着他的鼻子骂了。他陷入了两难。最终,在父皇的震怒下,赵元昊被投入大牢,
赵文渊停职待参。萧景恒不得不站出来,
说了几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定要严查”的场面话,但谁都能看出他的勉强和憋屈。
一场原本可以压下去的纨绔子弟伤人案,因为时机、地点、人物的巧妙安排,
变成了一场对准萧景恒势力核心的精准打击。我依旧沉默,甚至在有人试图将话题引向我,
暗示我可能借此攻击兄弟时,我只是淡然表示:“国法如山,自有公断。儿臣相信父皇圣明。
”但我知道,裂痕已经产生。赵文渊会怪萧景恒保他保得不够尽力,
萧景恒则会怨赵文渊教出这么个蠢儿子拖他后腿。猜忌的种子一旦种下,
就会在利益的温床上悄然生长。回到东宫,夜凉如水。曹谨言低声道:“殿下,
赵家派人送来了厚礼,
说是感谢殿下今日在朝堂上未曾落井下石……”我看着庭中摇曳的树影,笑了笑。看,
裂痕的另一边,已经开始试图寻找新的依靠了。“原封不动退回去。”我冷声道,
“告诉来人,孤,什么都不知道。”现在,还远不是收网的时候。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第五章:火种赵元昊的案子,像一块投入死水潭的石头,激起的涟漪远比表面看到的要深远。
赵文渊停职在家,其门生故吏人心惶惶,萧景恒一党气焰受挫,
朝堂上出现了短暂的、微妙的平衡。但这平衡脆弱不堪。我深知,仅靠一次离间,
不足以撼动根基。我需要更实在的东西,需要能一击毙命的武器。这武器,不能是流言,
不能是猜测,必须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的东西。我的目光,投向了北疆。前世,
大约在一年后,会爆发一场巨大的边患丑闻。镇北侯,也就是萧景恒的舅舅,
克扣军饷、倒卖军粮、杀良冒功的罪行会彻底败露,引发边军哗变,震动朝野。
那也是萧景恒势力遭受的一次重创,虽然最终他断尾求生,抛弃了舅父,但已元气大伤。
而这一世,我等不了一年。我要让这把火,提前烧起来,并且要让它按照我的意愿,
烧向指定的目标。契机,就在眼前。前世此时,北疆虽无大战,但小股蛮族扰边不断。
镇北侯麾下有一员名叫胡琏的参将,性情刚直,因不满上官贪墨,曾试图上书揭发,
结果奏折被中途截下,他本人也被寻了个由头,差点死在战场上。后来边患爆发,
他成了揭发镇北侯的关键证人之一。胡琏,就是我要找的“火种”。而他现在,正身处绝境,
急需一根救命稻草。“谨言,我们存在永兴票号的银子,动用起来可方便?”我问道。
“回殿下,票号认凭证不认人,手续齐备即可,十分隐秘便宜。”曹谨言答道。“好。
”我取出一枚看似普通、实则内有玄机的私人小印,“你亲自去一趟,取一万两现银,
换成小面额的通兑银票。
再找一支绝对可靠、最好是和军中有些关系、但又查不到我们头上的商队。
”“殿下的意思是……?”“让商队北上,目的地,北疆凉州。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
”我压低了声音,一字一顿,“找到参将胡琏,在他最困难、最孤立无援的时候,
‘偶然’帮助他,解决他的燃眉之急,比如,他手下弟兄的抚恤,他家人的饥寒。
但不要暴露身份,只说是敬佩胡将军的为人。”雪中送炭,远胜锦上添花。
我要在胡琏对镇北侯乃至整个朝廷彻底绝望之前,给他送去一丝微光,一丝希望,让他知道,
这世上并非全是污浊,还有人记得他们这些浴血边关的将士。“帮助要巧妙,要让他感激,
却不知感激谁。然后,”我顿了顿,眼中闪过冷光,“‘无意中’让他知道,
他之前那封被截下的奏折,并非石沉大海,而是……落在了某位‘有心人’手里,
这位有心人,正在暗中收集镇北侯贪墨军资、构陷忠良的证据。”曹谨言瞳孔微缩:“殿下,
您这是要……引他主动递上投名状?”“不完全是。”我摇摇头,“我要让他觉得,
他不是在背叛谁,而是在寻找一个可以申冤的途径,
一个能铲除军中蛀虫、还边关朗朗乾坤的契机。我们要做的,是提供一个渠道,一个保证,
保证他提供的证据,能够直达天听……或者,至少能送到足以扳倒镇北侯的人手中。
”我要让胡琏自己选择,是继续沉默等死,还是抓住这根看似渺茫的稻草,拼死一搏。
而我要的,就是他拼死一搏时,
些证据——镇北侯党羽贪污的账本明细、克扣军饷的往来书信、甚至是杀良冒功的地点记录。
这些,才是真正的火种,足以将萧景恒的外戚势力烧成灰烬的火种。“此事关系重大,
环节众多,务必谨慎,宁缓勿急。”我郑重叮嘱,“挑选的人,要万分可靠。银钱用度,
不必吝啬,但每一笔去向,都要有合理的解释。”“老奴明白!”曹谨言神色凝重,
“定会寻那行走北地多年、信誉卓著的老商号,用押送皮毛药材的名义北上,
绝不会引人怀疑。”计划悄然启动。一支看似普通的商队,带着充足的银钱和特殊的使命,
混在往来北疆的人流中,向着凉州而去。我坐在东宫,依旧每日读书习政,
仿佛对外界风云一无所知。但我知道,一颗棋子已经落下。胡琏就是那颗关键的棋子。
他现在是一簇微弱的火苗,在边关的寒风中摇曳。而我,要给他送去燃料,送去东风,
让他最终燃成冲天烈焰,烧向该烧的地方。这需要时间,需要耐心。但我最不缺的,
就是耐心。从地狱归来的人,等的起。偶尔,我会收到曹谨言递来的、没有落款的密报,
上面用只有我懂的方式,记录着商队的行程,
以及北疆零星传来的、关于胡琏近况的模糊消息——他似乎挺过了一次针对他的阴谋,
他麾下士卒的粮饷似乎短暂地充足过,他沉默的脸上,
似乎多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决绝……每一次看到这些消息,我都仿佛能看到,那遥远的北疆,
黑暗的帷幕之后,一点猩红的火种,正缓缓积蓄着力量,等待着燎原的那一刻。我端起茶杯,
抿了一口已经微凉的茶水。火种已埋下,只待东风起。第六章:风起胡琏那边如同石沉大海,
暂时没有新的消息传回。北疆遥远,通信不便,我虽有先知,却也无力改变物理的距离,
只能耐心等待火种慢慢燃烧。然而,京城的风,却不会因为北疆的寂静而停歇。
赵元昊的案子,在经过初期的剧烈震荡后,并未如寻常风波般渐渐平息,
反而在暗处酝酿着新的波澜。萧景恒显然不甘心吃下这个闷亏。他保下赵文渊的代价不小,
在父皇和清流心中都失了分,这让他恼火不已。他不敢,也不能直接对我这个太子发作,
于是,所有的怒火便转向了那个捅破天的御史——刘铭。这一日,
我正在文华殿听翰林学士讲解《资治通鉴》,说到党锢之祸,正是精妙处,
殿外却传来一阵隐隐的骚动。不多时,一个内侍匆匆而入,在主讲学士耳边低语几句。
那学士脸色微变,挥挥手让内侍退下,讲课的声音却不如先前沉稳了。我端坐不动,眼观鼻,
鼻观心,心中却如明镜一般。来了。果然,散学后,曹谨言便悄无声息地凑近,
低声道:“殿下,出事了。刘铭御史今日在早朝时,被数名言官联名弹劾,
罪名是……收受商人贿赂,构陷朝廷大员之子。”我脚步未停,嘴角却勾起一丝冷笑。构陷?
真是恶人先告状。萧景恒的反击,倒是来得又快又狠。这罪名安得巧妙,
将赵元昊打死人的事实模糊化,转而攻击刘铭的动机不纯,试图将一桩铁案扭转为朝臣倾轧。
“弹劾他的人,都是谁?”我淡淡问道。“领头的是吏科给事中王焕,
还有都察院内部两个素与刘铭不和的御史。这王焕,是赵尚书一手提拔起来的。
”曹谨言语速很快,“他们呈上了所谓‘商人’的证词和银票往来记录,做得有鼻子有眼。
”“刘铭如何反应?”“刘御史当场就炸了,在朝堂上直斥他们污蔑忠良,是赵文渊的走狗,
差点就要动手……被同僚拉住了。陛下龙颜大怒,已下令将刘铭停职,交由三法司会审。
”停职会审。无论结果如何,刘铭的仕途,短期内算是完了。萧景恒这一手,既是报复,
更是震慑,是做给所有可能想学刘铭“直言”的人看的。“我们……”曹谨言试探着问,
“要不要做点什么?刘御史毕竟是因……”“因我而起?”我打断他,停下脚步,
看向宫墙一角湛蓝的天空,“不,他是因心中的公道和法度而起。我们什么都不要做。
”“可是殿下,若刘铭被坐实罪名,那赵元昊的案子恐怕……”“赵元昊打死人是事实,
众目睽睽,刘铭不过是揭发者。萧景恒能泼脏水给刘铭,却抹不掉赵元昊的罪。最多,
就是让赵文渊官复原职的速度快一些罢了。”我冷静地分析道,“我们现在插手,
才是引火烧身。萧景恒巴不得我们跳出来保刘铭,正好坐实他‘构陷’的指控,
将矛头引向我。”我要的,从来不是靠一个耿直的御史去扳倒谁。刘铭是一把刀,用过了,
卷刃了,就该收回鞘中,或者……弃之。更何况,这把刀太过刚直,容易伤到自己,
本就不是我能完全掌控的。“让风再吹一会儿。”我轻声道,“看看这阵风,
能吹乱多少人的阵脚。”接下来的几日,朝堂上果然风波不断。
支持刘铭的清流官员和依附萧景恒的官员互相攻讦,口水仗打得不可开交。父皇被吵得头疼,
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但明显对惹出风波的刘铭更为不满。赵文渊虽未复职,
但气色好了许多,门下官员又开始活跃起来。而萧景恒,似乎很满意自己操控局面的能力,
姿态重新变得从容。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甚至对萧景恒更为有利。但我知道,
有些东西不一样了。那层看似牢固的联盟,已经被我撕开了一道细微的裂痕。
赵文渊见识了萧景恒“断尾”的果断虽然尾是他儿子,心中真无芥蒂?
那些依附萧景恒的官员,看到刘铭的下场,下次再遇到类似事情,
是否还会毫不犹豫地当马前卒?猜忌和恐惧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会自己生长。
我依旧每日读书、议事,对朝堂风波不置一词,甚至当父皇询问我对刘铭一案的看法时,
我也只是中庸地表示:“相信三法司定能查明真相,既不使忠良蒙冤,亦不令国法受损。
”扮演一个顾全大局、不偏不倚的太子,对我来说驾轻就熟。直到这天夜里,
曹谨言带来一个意外的消息。“殿下,北边……有消息了。”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压抑的激动。
我放下手中的书卷:“说。”“不是通过商队,是……沈墨。”曹谨言低声道,
“他今日主动找到了我们安排接触他的人,虽然依旧不知道殿下身份,但他透露了一个消息。
他在整理甲字库旧档时,发现了一批三年前北疆军械调拨的原始记录副本,其中一些数字,
与当年兵部核销的账目……对不上,差额巨大。他怀疑,其中有人做了手脚,贪墨了军资。
”沈墨?竟然是沈墨!我眼中精光一闪。这真是意外之喜!
我原本只是在他身边埋下一颗闲棋,没想到,这颗棋自己却找到了一条大鱼!
三年前的军械账目……那正是镇北侯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胡琏那边的火种尚未燃起,
沈墨这边,却意外地送来了一股东风。“那些记录副本,能弄到手吗?”我立刻问道。
“沈墨很谨慎,他只是透露了此事,并未交出副本。他说……他要见能做主的人。
”曹谨言道,“他似乎猜到背后不简单,想谈条件。”我沉吟片刻。沈墨这是要借力,
借我这把不知道是谁的“刀”,去斩他心中的奸佞。他有风骨,但也有读书人的执拗和算计。
“告诉他,”我做出决定,“东西保管好,静待时机。至于做主的人……时机到了,
自然会出现。另外,从票号支一千两银子,匿名给他,
就说是资助他继续‘梳理’库档的茶水钱。”不能急,不能轻易现身。
但可以给他更多的资源和暗示,让他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沈墨找到的这批账目,
或许不如胡琏未来的证词有冲击力,但作为辅证,却能极大地增强说服力。山雨欲来风满楼。
京城的波澜未平,北疆的火种暗燃,如今又多了一条来自陈旧档案里的线索。风,
已经吹起来了。而且,是从不同的方向。我走到窗边,夜风带着凉意吹入。局势,
似乎变得越来越有趣了。第七章:云涌沈墨带来的消息,像一块巨石投入我心湖,
激起的却是一片死寂的涟漪。表面平静,内里已是暗流汹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