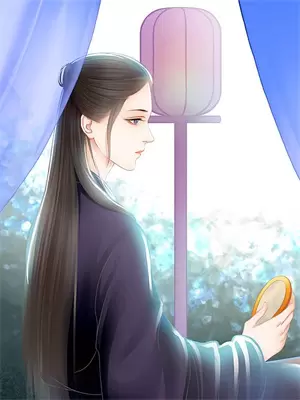
---民政局那扇巨大的玻璃门,像一块冰冷的、隔断生死的界碑。门内,
是顾沉舟递过来的离婚协议,纸张崭新得刺眼,散发出油墨和某种无情决定的混合气味。
门外,铅灰色的天空沉沉压下来,酝酿着一场夏末的暴雨,湿漉漉的风裹挟着尘土的气息,
黏腻地扑在皮肤上。“签了吧,林晚。”顾沉舟的声音没什么起伏,
像在陈述一件与己无关的日常琐事。他微微侧身,露出臂弯里紧紧依偎着的年轻女人。
那女人穿着当季最新款的连衣裙,妆容精致得无可挑剔,
此刻正用一种混合着怜悯与毫不掩饰的轻蔑眼神,上下扫视着我,
仿佛在评估一件过时的、亟待处理的旧家具。她的红唇轻启,
吐出的字眼却像淬了冰的针:“就是呀,姐姐。拖着对谁都不好,何必呢?
你这种……”她故意停顿了一下,涂着鲜红蔻丹的手指轻轻拂过顾沉舟昂贵西装的袖口,
“围着灶台转的家庭主妇,离了沉舟,怕是连星衍的奶粉钱都挣不出来吧?沉舟也是可怜,
还得养着你们母子俩。”空气凝滞得让人窒息。顾沉舟没有反驳,甚至没有看她一眼,
只是将目光投向我握着笔的指尖,带着一种近乎冷酷的催促。我垂着眼,
目光落在协议书上“财产分割”那一栏。
上面清晰地写着:女方自愿放弃所有共同财产分割权。墨黑的字迹,像一条条冰冷的锁链。
指尖下的笔杆冰凉,却远不及心口那片早已荒芜的冻土。没有犹豫,
也没有再看眼前这对璧人一眼。笔尖划过纸面,发出沙沙的轻响,
利落地签下“林晚”两个字。最后一笔落定,
仿佛也斩断了心底最后一丝微弱到几乎不存在的牵连。就在这时,
一个清脆稚嫩、带着点急切和兴奋的童音,穿透了玻璃门沉闷的隔音,
清晰地钻了进来:“妈妈!妈妈!你的布加迪停错车位啦!保安叔叔说要贴条啦!
”声音来自我脚边——不知何时溜到了门口的儿子,顾星衍。小家伙五岁了,正踮着脚尖,
小脸贴在冰凉的玻璃上,努力地朝外张望着,小手还焦急地拍打着门。
这声音如同一颗投入死水的石子。顾沉舟和他臂弯里的女人同时一怔,
目光下意识地顺着星衍手指的方向,穿透巨大的落地玻璃窗,投向民政局门前的停车场。
那里,一辆线条凌厉如猛兽、通体泛着神秘幽蓝色泽的超跑,
静静地泊在离门口最近的那个、明晃晃标注着“访客临时停放”的车位上。
午后的天光被厚重的云层切割得支离破碎,却恰好有几缕,吝啬地洒落在那辆车的车身上。
车身表面镶嵌的钻石如同星河倾泻,折射出令人目眩神迷的璀璨光芒,
每一道光线都像无声的嘲讽,狠狠地抽在刚才那番“奶粉钱”的言论上。
时间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我清晰地看到,顾沉舟眼底掠过一丝极深的困惑,
眉头下意识地蹙起,
这辆价值难以估量的豪车与他认知里那个“连奶粉钱都挣不出”的前妻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而他臂弯里的女人,那张精心描绘的脸庞,血色如同退潮般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
只剩下一种惊恐的惨白。她的眼睛瞪得极大,死死地黏在那辆布加迪上,红唇微张着,
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喉咙,连呼吸都停滞了。死寂。
民政局大厅里人来人往的嘈杂仿佛被无形的屏障隔绝了,
只剩下我们几人之间这片令人窒息的真空。我弯下腰,
动作轻柔地把还在兴奋地拍打玻璃门的儿子抱了起来。
小家伙很自然地伸出胖乎乎的小胳膊搂住我的脖子,小脑袋亲昵地靠在我肩膀上,
一双黑葡萄似的大眼睛好奇地转着,看看外面那辆漂亮得不像话的车,
又看看脸色难看的爸爸和那个陌生的阿姨。我抱着他,转过身,
目光平静地迎上顾沉舟和他女伴那双写满震惊与难以置信的眼睛。唇角,
慢慢勾起一个极其浅淡、几乎看不出弧度的笑容。“哦,那个啊。”我的声音不高,
甚至带着点漫不经心的慵懒,清晰地穿透了这片凝固的空气,“抱歉,
家里的保姆早上开去买菜,可能太赶时间了,没注意车位。我待会儿让她挪一下。”“保姆?
买菜?”女人尖利的声音陡然拔高,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充满了荒谬感和被羞辱的愤怒,
“你开什么玩笑!那是布加迪!镶钻的限量款!”她的失态引来周围几道好奇探究的目光。
顾沉舟的脸色也彻底沉了下去,眼神锐利如刀,紧紧锁住我,
仿佛要从我脸上找出任何一丝说谎的痕迹。我没有理会她的尖叫,只是低头,
用指尖轻轻蹭了蹭儿子柔嫩的脸颊:“星衍,书包呢?外婆昨天给你的那个小布包,
里面是不是有本画画的小本子?妈妈看看你画的什么。”“在这里,妈妈!
”星衍立刻扭动小身子,从我怀里滑下去一点,
献宝似的拉开他那个印着小恐龙的、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双肩小书包。小手在里面摸索着,
很快,掏出了一本……比普通画册厚实得多、封面是暗蓝色硬皮的本子。那本子有点旧了,
边角微微磨损。星衍很认真地把它递给我:“外婆说,这个本子很重要的,让我放好。
”我接过来,手指随意地翻开一页。动作自然得像是在检查孩子的涂鸦。然而,
当那翻开的一页内容暴露在顾沉舟和他女伴的视线中时,时间仿佛再次被冻结。那不是涂鸦。
那是一份打印得异常清晰的医院诊断报告书。纸张顶端,是本市最顶级私立医院的烫金徽标。
报告内容里,“顾沉舟”三个字,被加粗的打印体清晰地标注在患者姓名栏。
而紧随其后的诊断结论,如同最冰冷的死亡宣判,带着一种残酷的精准,
烙印在纸上:**肝细胞癌HCC,IV期晚期。****预后极差。**风,
似乎在这一刻彻底停了。民政局大厅里中央空调运作的微弱嗡鸣声,变得无比清晰刺耳。
顾沉舟脸上的血色,褪得比刚才他女伴还要彻底。那张英俊却透着疲惫的脸上,
所有的表情瞬间被抽空,只剩下一种近乎空白的茫然和难以置信的震骇。
他的瞳孔骤然收缩到极致,死死地钉在那份报告书上,仿佛要把那几行字烧穿。
他下意识地朝我,或者说朝那份报告书的方向,猛地跨前一步,身体微微前倾,
伸出的手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似乎想立刻夺过去确认。
他身边的女人更是惊得倒抽一口冷气,下意识地捂住了嘴,眼睛瞪得几乎要裂开,
看看那份报告,又惊恐地看看顾沉舟瞬间惨白的脸,
仿佛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己挽着的这个男人身上潜伏着多么可怕的阴影。“这……这是什么?
”顾沉舟的声音干涩得厉害,像是砂纸在摩擦,“谁……谁的?
”我的视线终于从报告书上抬起,平静地落在他那张写满惊骇的脸上。没有悲伤,没有愤怒,
只有一种近乎于漠然的平静,像是在看一个与己无关的陌生人。“你的。”两个字,清晰,
简短,如同两枚冰锥,精准地刺入他此刻脆弱不堪的心脏。他的身体剧烈地晃了一下,
像是被无形的重锤狠狠击中。那份高高在上的冷漠和掌控感,在这一刻彻底粉碎。
他死死地盯着我,嘴唇哆嗦着,似乎想说什么,质问、咆哮、或者别的什么,
但最终一个字也没能吐出来。巨大的恐惧和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瞬间攫住了他。
“不……不可能!”他身边的女人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带着尖锐的、试图否认现实的颤抖,“沉舟他好好的!你伪造的!林晚,
你伪造这个想干什么?想吓唬谁?!”伪造?我懒得再看他们一眼,更懒得解释。
只是将那份沉重的报告书随意地合上,重新塞回儿子的小书包里,拉好拉链。然后再次弯腰,
把懵懂地看着这一切的儿子稳稳地抱了起来。“星衍,我们回家了。
理会身后那两道如同实质般钉在我背上的、充满了震惊、恐惧、愤怒和无数复杂情绪的目光,
我抱着儿子,步履从容地走向那扇通往外面风雨世界的玻璃门。
厚重的玻璃门无声地自动滑开。外面,酝酿已久的暴雨,终于倾盆而下。
豆大的雨点狂暴地砸在柏油路面上,溅起无数浑浊的水花,发出震耳欲聋的哗哗声。
天地间一片迷蒙的水汽,瞬间模糊了视线。冰冷的雨水裹挟着狂风,劈头盖脸地打来,
瞬间就浸透了我单薄的衣衫,带来刺骨的寒意。我下意识地将怀里的儿子搂得更紧了些,
用身体尽量为他挡住风雨。小家伙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大雨和刚才的气氛吓到了,
把小脸深深埋进我的颈窝,小手紧紧抓着我的衣领。那辆幽蓝色的布加迪威龙,
如同风雨中蛰伏的巨兽,静静地停在几步开外。流线型的车身在雨水的冲刷下,
钻石的光芒更加迷离而冷冽。我抱着儿子,快步走向驾驶位一侧的车门。
雨水疯狂地打在脸上,几乎睁不开眼。
就在我的手即将触碰到车门把手的那一刻——一个身影如同失控的炮弹,
猛地从民政局大门内冲了出来,完全不顾那足以将人瞬间浇透的暴雨,
跌跌撞撞地扑到了我的车前。是顾沉舟。昂贵的西装被雨水彻底浸透,湿漉漉地紧贴在身上,
勾勒出他此刻狼狈而绝望的轮廓。精心打理的发型早已凌乱不堪,
雨水顺着他的额发、脸颊、下巴不断流淌。他脸上毫无血色,嘴唇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灰白,
那双曾经总是带着疏离和掌控感的眼睛,此刻布满了骇人的红血丝,
死死地、如同濒死的野兽般盯着我。“林晚!”他的声音在震耳欲聋的雨声中撕裂开来,
带着一种濒临崩溃的嘶哑和绝望的质问,“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早就知道了?!什么时候?
!”他像疯了一样,用拳头狠狠砸向我面前的车窗玻璃,发出沉闷而绝望的“砰砰”声。
雨水顺着他挥拳的手臂疯狂流下,混着一种说不清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液体。“为什么?!
你说话啊!”他的拳头砸在坚硬的防弹车窗上,指节瞬间泛红破皮,渗出血丝,
又被雨水迅速冲刷稀释。那疯狂的动作和嘶吼,在瓢泼大雨中显得格外凄厉和无力。
隔着被雨水不断冲刷、变得模糊扭曲的车窗,我看着他此刻如同困兽般绝望挣扎的模样。
那张曾经令我迷恋、也最终将我推入深渊的脸,
此刻只剩下狼狈、恐惧和一种被命运玩弄的愤怒。心底最后一丝微弱的涟漪,
也彻底归于死寂。怀里的儿子似乎被这疯狂的砸窗声吓到了,小身体在我怀里瑟缩了一下,
发出一声小小的呜咽。我低下头,用脸颊轻轻贴了贴他冰凉的小额头,无声地安抚着。然后,
我抬起了没有抱着孩子的左手。没有去开车门,也没有去擦脸上的雨水。我的左手无名指上,
不知何时,多了一枚戒指。一枚设计极其简洁、却又在漫天灰暗雨幕中,
骤然迸发出惊人火彩的钻戒。硕大的主钻纯净无瑕,切割完美,即使在这昏暗的暴雨天里,
也如同将一束凝固的星光戴在了指间。戒圈是低调的铂金,
内圈似乎还刻着某种极细小的字母。车窗外的顾沉舟,砸窗的动作猛地僵住了。
他那双布满血丝、写满疯狂质问的眼睛,瞬间被那枚戒指的光芒刺得瞳孔骤缩,
脸上所有的表情都凝固了,只剩下一种被彻底击垮的茫然和难以置信。我隔着模糊的雨幕,
平静地迎上他碎裂的目光,声音不大,却清晰地穿透了哗哗的雨声,
带着一种淬了冰的寒意:“告诉你?”我的唇角甚至勾起了一抹极淡、极冷的弧度。
“告诉你,然后让你躺在病床上,看着我用你的遗产,养我的新男人和孩子吗?
”我的目光扫过他砸在车窗上、指节已经破皮流血的手,“顾沉舟,等你死了,这笔遗产,
正好。”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冰棱,精准地扎进他此刻最脆弱的心脏。
顾沉舟像是被这句话彻底抽走了所有的力气和灵魂,砸窗的手颓然垂下,
整个人如同断线的木偶,踉跄着向后倒退了半步,失魂落魄地站在狂暴的雨幕中。
雨水无情地冲刷着他惨白的脸,混合着某种液体流下,分不清是雨是泪。他看着我,
眼神空洞,仿佛第一次真正认识眼前这个他曾经弃如敝履的女人。
“滴——”我按下了车钥匙的开锁键。清脆的电子音在雨声中格外清晰。
驾驶座的车门锁应声弹开。然而,还没等我伸手去拉车门——副驾驶的车门,
却被人从里面轻轻推开了。一个颀长挺拔的身影,从容地从驾驶座那边绕了过来,
撑开一把宽大的黑伞,精准地罩在了我和儿子头顶,瞬间隔绝了狂暴砸落的雨点。伞下,
出现一张年轻而极其英俊的脸。鼻梁高挺,眉眼深邃,
气质温润中带着一种医者特有的清冷和沉稳。他穿着剪裁合体的浅色休闲西装,
肩头落了几点雨水,却丝毫不显狼狈。他看也没看僵在雨中的顾沉舟,
仿佛那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路障。他的目光径直落在我怀里的星衍身上,
带着一种自然而然的关切和温柔。“星衍,吓到了?”他的声音清朗悦耳,
带着安抚人心的力量。随即,他极其自然地弯下腰,动作熟练而轻柔,
伸手去帮星衍整理因为埋在我怀里而蹭歪了的小书包带子,
又仔细地掖好包裹着孩子的小毯子一角,确保没有一丝风雨能侵袭到孩子。“不怕,叔叔在。
”他对着星衍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然后才抬眼,
目光平静无波地扫向挡在车前、如同泥塑木雕般僵立的顾沉舟。那眼神,没有任何轻蔑,
也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医生面对陌生病人时纯粹的、职业性的疏离。他的声音不高,
却清晰地穿透雨幕,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理所当然的驱赶意味:“麻烦让一让,顾先生。
”他微微侧身,示意了一下驾驶座的方向,
语气平淡得像在陈述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你挡着路了。我得送星衍去医院打疫苗,
预约的时间快到了。”---顾沉舟如同被那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抽走了所有骨头,
踉跄着倒退一步,整个人像一尊被暴雨冲刷的泥塑,僵立在原地。雨水无情地砸在他脸上,
冲刷着他惨白的面孔和指关节渗出的血丝,狼狈不堪。他空洞的眼神死死钉在我脸上,
那里面翻涌着太多东西——难以置信、被彻底愚弄的愤怒、灭顶的恐惧,
以及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迟来的悔恨?可惜,太晚了。
“滴——”解锁声清脆地刺破雨幕。驾驶座的车门锁弹开。然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