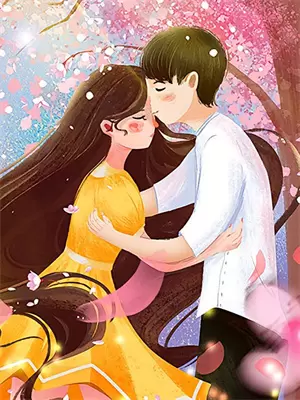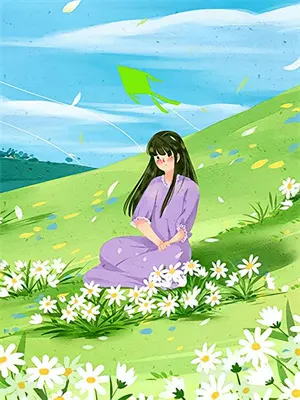
1 午夜来电林远回到这栋位于江南水乡老镇深处的宅子时,天空正飘洒着绵密如丝的梅雨。
雨水顺着黛瓦滴落,在长满青苔的石阶上溅起细碎的水花,
空气里混杂着潮湿的木头、陈年旧书以及一丝若有若无的霉味,
那是外婆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独有的气息,也是外婆身上他最为熟悉的味道。
外婆去世已经整整一个月了。作为大学里最年轻的副教授,
林远一直被繁杂的校务和科研项目缠身,直到学期结束,才勉强抽出一段完整的时间,
回到这座空置已久的老宅,整理外婆的遗物。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
时光仿佛在这里凝固了。客厅里的陈设一如既往,
藤编的沙发、泛黄的字画、擦拭得一尘不染的八仙桌,一切都保留着外婆生前的样子,
只是少了那个总是笑眯眯等着他回来的身影。他的目光落在客厅角落那个核桃木茶几上。
一台老式的象牙白拨盘电话机,像一只温顺的、沉睡中的宠物,静静地趴在那里。
林远有些诧异,在这个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
这种需要手指插进转盘里一圈圈拨号的古董,早就该被淘汰了。他记得自己上中学时,
就曾建议外婆换一部带按键的电话,却被外婆以“用惯了”为由婉拒。没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它竟然还在这里,而且被擦拭得光洁如新,仿佛随时等待着铃声响起。
夜深了。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敲打着玻璃窗,如同永无止境的低语。林远坐在地板上,
周围散落着好几本厚重的旧相册。
他正试图将那些记录着家族历史的黑白或泛彩照片分门别类,
指尖拂过照片上外婆年轻时的容颜,心头萦绕着淡淡的感伤。就在这时,
一阵突兀的、极其清脆响亮的铃声,陡然划破了老宅的寂静。
“叮铃铃——叮铃铃——”声音的来源,正是那台老式拨盘电话。林远的心猛地一跳,
几乎要撞出胸腔。这电话的线路,不是早在几年前就被电信公司通知停用了吗?
或许是邻居有急事,用了某种特殊的方式接通?他带着疑惑,犹豫地站起身,走到茶几旁,
那铃声持续不断地响着,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他深吸一口气,
伸手接起了那个沉甸甸的听筒,将它贴近耳朵。“喂?”他试探着问道。
电话那头没有任何人声回应,只有一种奇怪的、类似无线电干扰的“沙沙”声,绵长而空茫,
仿佛信号正艰难地穿越一片无尽的、没有星辰的虚空,带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寂寥。“喂?
请问你找谁?”林远定了定神,又问了一遍,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一些。几秒钟后,
那“沙沙”的干扰声似乎减弱了一些,一个极其微弱、失真严重、仿佛来自遥远天际的声音,
断断续续地传来:“远……远儿……是……是囡囡吗?”“囡囡”是他的小名,
是外婆在他蹒跚学步时就开始叫的称呼,这世上会这么叫他的,只有外婆一个人。
而这个声音……虽然微弱、扭曲,仿佛隔着千山万水,还夹杂着电流的杂音,
但林远在一瞬间,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这分明就是外婆的声音!
更让他感到心悸的是,
那声音里透着一股他从未在外婆身上听到过的、属于孩童般的怯生生和迷茫,
像是一个走丢了的小女孩在无助地呼唤。“外婆?是……是您吗?
”他的声音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握着听筒的手心沁出了冷汗。这太荒谬了,
外婆已经去世一个月了,这怎么可能?“……冷……好黑呀……”声音变得更加模糊不清,
带着细微的哭腔,随即被一阵更强烈的“滋啦”电流声所淹没,然后,电话突兀地断了,
听筒里只剩下单调而急促的忙音,“嘟——嘟——嘟——”。林远握着已经失去信号的听筒,
呆呆地站在原地,心脏在胸腔里狂跳不止,耳边似乎还回荡着那声稚嫩的“囡囡”。
是幻觉吗?是因为最近太劳累,加上对外婆过度思念而产生的幻听?
还是某个知晓内情的人搞的、极其拙劣恶劣的恶作剧?他下意识地抬起手腕,看了看表,
荧光指针刚好指向晚上十一点整。2 记忆碎片这一夜,林远辗转反侧,
窗外的雨声和那声“囡囡”在他的脑海里反复交织,直到天色微亮,他才迷迷糊糊地睡去。
第二天,林远在处理旧物时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他时不时地瞥向那台静默的电话机,
心中混杂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期待和一丝隐隐的恐惧。他甚至去检查了电话线,
接口处有些老化,但确实连着墙上的端口,至于线路是否通畅,他无从得知。夜幕再次降临,
雨依旧下着。林远刻意守在了电话旁的藤椅上,手里拿着一本书,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接近十一点时,他不自觉地坐直了身体,屏住了呼吸。
当时钟的指针精准地重合在十一点的刻度时,“叮铃铃——”,熟悉的铃声再次骤然响起,
在这寂静的夜里,如同一声宣告。林远深吸了一口气,像是要赴一个重要的约会,
迅速而坚定地接起了电话。“沙沙”的干扰声依旧存在,但似乎比昨晚稳定了一些。
外婆的声音再次传来,依然带着孩童特有的、软糯的哭腔,
但吐字清晰了不少:“……妈妈……我的蝴蝶发卡……找不到了……红色的,
上面有亮晶晶的……像糖纸一样……”蝴蝶发卡?林远蹙起眉头,在记忆里快速搜索,
却毫无印象。外婆从未跟他提起过童年时拥有过这样一枚发卡。他试图引导对话,
追问更关键的信息:“外婆,您在哪里?您还好吗?您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玩……说我的衣服是旧的……是捡姐姐穿剩下的……”电话那头的声音充满了委屈和失落,
完全沉浸在一个小女孩被同伴孤立后的伤心情绪里,对他的问题置若罔闻。然后,
信号再次开始不稳定,在一阵逐渐加强的“滋啦”声中,通话被迫中断。林远缓缓放下听筒,
陷入了巨大的困惑之中。这绝不像是恶作剧,
有谁会编排如此古怪、私人且充满童年细节的内容来戏弄他?他想起外婆晚年时,
偶尔会坐在院子里,对着蓝花楹树,念叨一些模糊的童年往事,大多是零碎的片段,
但确实从未提及过什么红色的蝴蝶发卡。这通电话,
仿佛打开了一条通往外婆遥远记忆的缝隙。第三天晚上,十一点整,铃声如期而至。这一次,
电话里的“外婆”似乎长大了一些,声音里的稚气稍褪,变成了少女清亮而带着忧思的语调。
“……报考师范的事情,爸爸不同意……他想让我学医……说当医生稳定,
受人尊敬……可我更喜欢当老师,教孩子们唱歌、识字,
看着他们一点点长大……”这次的通话时间比前两次稍长一些,
少女的声音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与对家庭阻力的淡淡烦恼。林远握着听筒,心中震动。
外婆退休前,正是镇上那所中心小学里备受爱戴的语文老师,桃李满天下。他小时候,
常听母亲说起外婆是如何耐心教导每一个学生。原来,这份职业,
竟是她年轻时经过抗争才得以坚持的梦想。他第一次,通过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
触碰到了外婆遥远青春时代的人生片段,感受到了她那时的坚持与迷茫。
3 时光回响他开始清晰地意识到,这些深夜来电,或许并非随机的、孤立的灵异事件。
它们更像是一盘散乱的、记录着生命轨迹的录音带,正被一种未知的力量,从某个起点开始,
可能是逆向,也可能是顺序地,播放着外婆存储在时光深处的记忆碎片。接下来的日子,
每晚十一点的电话,成了林远生活中唯一且最重要的期待。他不再恐惧,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虔诚的守候。他准备好纸和笔,
像一个认真听讲、生怕漏掉任何一个知识点的学生,
将电话那头流淌出的每一个字、每一种情绪,都仔细地记录下来。电话里的“外婆”,
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快速而连续地经历着人生的各个重要阶段:有刚刚参加工作,
为了一次不理想的工作调动而烦恼的年轻女职员,
声音里充满了对未来的不确定;有在单位联谊会上,遇到了那位后来成为外公的同事,
陷入热恋的羞涩姑娘,语气中满是甜蜜与忐忑;有第一次确认怀上孩子时,
既兴奋雀跃又紧张不安的准妈妈,
小心翼翼地分享着孕育生命的喜悦……这些叙述往往是支离破碎的,跳跃的,
并且夹杂着极其强烈的“当下”情绪,仿佛打电话的人,并非在回忆,
而是正亲身经历着电话中所描述的那个时刻。林远的情感也从最初的震惊、恐惧,
逐渐转变为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动和珍惜。他仿佛获得了一张独一无二的“观影券”,
正在观看一场只为他一**人**放映的、关于外婆一生的私密电影,
这部电影由外婆本人“主演”并“配音”。他开始有意识地去求证这些从电话中获取的信息。
他重新翻出那些旧相册,戴上眼镜,借助台灯的光芒,一页页仔细搜寻。果然,
在一张边角已经磨损的黑白全家福里,年幼的外婆站在中间,
头上依稀别着一枚小小的、形状似蝴蝶的发卡,虽然颜色无法分辨,但那模糊的轮廓,
与电话中描述的“红色、有亮晶晶”的饰物极为吻合。他心中一震,
指尖轻轻拂过照片上那张稚嫩的脸庞。
他还设法联系上了几位仍住在镇上的、与外婆年纪相仿的老邻居,
在闲聊中旁敲侧击地问起外婆年轻时的工作情况。
一位满头银发的阿婆眯着眼睛回忆道:“你外婆啊,刚参加工作时是在县里的文化站,
后来是自己坚决要求调到小学当老师的,为了这个,
还跟她父亲闹过一阵子别扭呢……”细节与电话中的叙述高度吻合。最让他动容的,
是那通提到母亲出生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充满了产后的疲惫,
却蕴含着巨大的、几乎要溢出来的幸福:“……是个女儿,六斤三两,头发乌黑,
眼睛像黑葡萄一样亮……我要叫她‘薇薇’,春薇,春天的蔷薇,多有生命力,
希望她像蔷薇花一样,美丽又坚韧……”林远走到书桌前,拿起母亲年轻时的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女子笑靥如花,眼睛果然又大又亮,如同浸在水里的黑葡萄。
他的泪水瞬间模糊了视线。母亲在三年前因病去世,走在了外婆的前面,
这让外婆晚年承受了巨大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如今,他竟以这种匪夷所思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