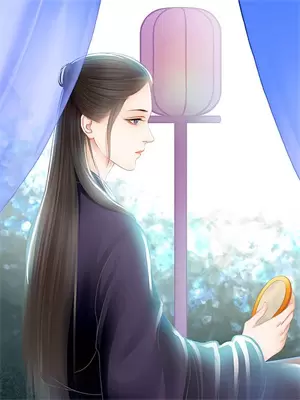嘘,祂在看着呢邻居家的小女孩死了,下身赤裸。她家人一口咬定是我那傻子哥哥做的。
可我知道,哥哥虽然傻,但连只蚂蚁都不忍心踩。从那天起,诅咒降临了。
女孩的爸爸在自家粮仓里被发现,浑身缠满了密密麻麻的渔线,勒得像一颗腐烂的石榴。
接着是她爷爷,淹死在半米深的猪食槽里,脸上带着诡异的笑。请来的道士刚做法就疯了,
用指甲抠烂了自己的眼睛,尖叫着“她身上趴着个黑的!”夜里,
女孩浑身湿透地站在我床头,递给我一个脏兮兮的布娃娃:“姐姐,下一个,轮到你了。
”1我们村,藏在山坳坳里,闭塞得连日子都过得比别人慢半拍。泥土墙,黑瓦片,
一条瘦狗常年趴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吐着舌头。空气里总是混杂着牲口粪便和柴火灶的味道,
一种沉甸甸的、属于土地的腥气。我家和根生家是邻居,院墙挨着院墙,这边摔个碗,
那边都能听见响。可心,却隔着十万八千里。我哥福来,因为我妈生他的时候难产,
大夫说是什么脑缺氧,生下来脑子就慢,村里人都叫他“傻福来”。他今年二十五了,
智力却像个五六岁的孩子。但在爹娘眼里,尤其是娘眼里,福来是心头肉,是命根子,
是老陈家传宗接代的独苗。就因为他是男的。而我,陈招娣,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个笑话。
我是爹娘盼儿子路上那个多余的丫头片子。在家里,我透明得像个影子,吃饭不能上桌,
有好吃的得紧着福来,活儿却一样不能少干。福来摔了跤,挨骂的是我,爹娘不开心了,
出气筒也是我。我习惯了,像墙角那丛野草,习惯了逆来顺受。福来傻,但不恶。
他最喜欢看蚂蚁搬家,能蹲在墙角看半天,然后咧着嘴傻笑,小心翼翼生怕踩到它们。
他怕黑,晚上得娘拍着才能睡着。这样的福来,
我怎么也无法把他和“强奸杀人”这四个字联系起来。可祸事,还是毫无征兆地砸了下来。
那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外面就炸了锅。哭喊声、咒骂声、砸东西的声音混成一片,
像是要把天捅个窟窿。我披上衣服跑出去,看见根生叔和他爹,
那个干瘦得像老核桃似的根生爷,正红着眼珠子往我家院里冲,我爹娘死死拦着。“陈老蔫!
你个狗日的!把你家那傻畜生交出来!他害死了我家英子!我操你祖宗!
”根生叔额头青筋暴起,手里攥着一把劈柴的斧头,样子要吃人。英子?根生家那个小女儿?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英子才八岁,瘦瘦小小的,平时见了人总是怯怯的,不怎么爱说话。
“放你娘的屁!我家福来连鸡都不敢杀看,能害你家英子?你再胡咧咧我撕了你的嘴!
”我娘像只护崽的母老虎,叉着腰挡在最前面,唾沫星子喷了根生叔一脸。“不敢?你看看!
你们自己看看!”根生爷跺着脚,手指向他们家院子方向,老泪纵横,
“英子……英子她……下身光溜溜的,就死在院墙根下!不是你家傻子干的能是谁?啊?
村里就他一个傻子!就他一个不干正经事的混子!”我爹怒目圆瞪,
却只会重复一句话:“没证据……没证据就不能瞎说……”场面乱成了一锅粥。
村里看热闹的人越围越多,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我透过人群的缝隙,看到根生家院门口,
英子她娘,那个总是低眉顺眼、瘦得一阵风就能吹倒的女人,正瘫坐在地上,像丢了魂似的,
眼泪早就流干了,只是无声地张着嘴,身子一抽一抽。最后,村长来了,好说歹说,
才把快要动起手的两家人拉开。派出所的人也来了,把英子的尸体抬走了,又问了话。
可就像根生爷说的,福来是个傻子,他的话不能当证据,现场又没找到什么像样的物证,
这事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成了悬案。但梁子,就这么结下了。
根生家一口咬定是福来害了英子,见我家人就骂。我家爹娘则觉得受了天大的冤枉,
憋着一肚子火。两家人从此成了死对头,连带着整个村子都弥漫着一股诡异的低压。福来呢?
他好像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是被那天早上的阵仗吓坏了,
有好几天都躲在屋里不敢出来,晚上睡觉时常惊悸哭醒,
嘴里含糊地念叨:“怕……英子……英子冷……”我当时只当他是吓糊涂了,
还摸着他的头安慰他:“哥,不怕,英子去好地方了,她不受苦了。”2英子的死,
像一块巨石投入死水,溅起了所有的恶臭淤泥,糊满了村里每个人心照不宣的秘密。
丧事办得简单又潦草,一口薄皮棺材,草草埋在了后山。根生家没再大闹,
但那沉默比吵闹更瘆人。根生叔和根生爷的眼神,像淬了毒的钉子,每次撞见,
都让我脊梁骨发冷。英子娘则彻底垮了,形销骨立,整日里像个游魂似的在村里飘荡,
见人就抓住问:“看见俺家英子没?她冷,俺得给她送件衣裳……”声音嘶哑,
听得人心里发酸。我家日子也不好过。爹娘出门都低着头,像是真做了什么亏心事。
他们对福来看管得更紧了,几乎不许他踏出院子一步,仿佛这样就能把流言蜚语挡在门外。
福来变得愈发沉默,常常一个人蹲在院子角落,对着蚂蚁窝发呆,一蹲就是半天。有时,
他会突然抬起头,没头没脑地问我一句:“妹,英子还回来不?她答应了要给俺编个蚂蚱。
”我心里堵得厉害。我是不信福来会做那种事的,可村里人那种异样的眼光,
像针一样扎在身上。有次我去井边打水,听见几个长舌妇在嚼舌根。“肯定是那傻子,
你没见英子死的那样子,啧啧,造孽啊……”“谁说不是呢,根生家真是倒了血霉,
摊上这么个邻居。”“陈老蔫家也不是好东西,养个傻子祸害乡邻……”我气得浑身发抖,
水桶咣当一声掉进井里,扭头就跑。身后传来她们压低了的、却更显刻薄的笑声。夜里,
我开始睡不踏实。总觉得窗外有影子晃,有时是英子娘幽幽的哭声,
有时又像是小孩细细的啜泣。我以为是风声,或是自己吓自己。直到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梦里,也是晚上,很冷,呵气成霜。我好像飘在半空,看见英子家那个破败的院子。
英子头发乱糟糟的,身上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单衣,光着脚,站在冰冷的泥地上。
她面前是她爹根生叔,喝得醉醺醺的,满嘴污言秽语,伸手要去扯她的裤子。
英子吓得像只小兔子,拼命往后缩,嘴里哀求着:“爹,俺冷,
俺要回屋……”根生叔不耐烦,一巴掌扇过去,英子瘦小的身子踉跄着撞在院墙上。这时,
根生爷那间屋的门开了条缝,那个老核桃似的脸在阴影里一闪,嘟囔了一句:“吵啥吵,
还不睡!”然后,门又关上了,冷漠得像关上牲口棚。英子趴在地上,小声啜泣。
根生叔骂骂咧咧,又上前踢了她一脚,大概是觉得扫兴,摇摇晃晃回自己屋了。
院子里只剩下英子一个人,蜷缩在墙根下,身子抖得像风中的落叶。天,越来越冷。
月光照在地上,泛着青白色。英子的哭声渐渐弱下去,嘴唇冻得发紫,脸上还挂着泪痕。
她伸出手,徒劳地想抓住什么,但只有刺骨的寒风。她的眼神开始涣散,
望着我家院墙的方向,嘴唇动了动,似乎想喊什么,却发不出声音。最后,她不动了。
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倒映着惨白的月亮,像两潭死水。我猛地惊醒,冷汗浸透了衣裳,
心脏狂跳不止。窗外,天还没亮,黑沉沉的。那个梦太真实了,英子临死前的眼神,
那种绝望和冰冷,清晰地烙在我脑子里。第二天,我精神恍惚,
忍不住把梦里模糊的片段告诉了我娘。我娘脸色瞬间变得难看,
劈头盖脸骂了我一顿:“死丫头!胡吣什么!做梦也当真?
肯定是白天听那些烂舌根的胡说八道听多了!我告诉你,不许在外头乱说!
还嫌家里不够乱吗?”我闭了嘴,心里却像压了块冰。那真的只是梦吗?英子死的那晚,
到底发生了什么?3平静,或者说死寂,并没有持续多久。怪事,开始一件接一件地发生,
目标直指根生家。先是根生家养了多年的老黄狗,在一个清晨被发现死在了院门口,
脖子被什么东西拧成了麻花,舌头伸的老长,眼珠子瞪得溜圆,满是恐惧。村里人私下议论,
说是冲撞了什么东西。但这,仅仅是个开场。第一场真正的恐怖,降临在根生叔身上。
那是个雾很大的早上,有人去根生家借农具,发现粮仓的门虚掩着,
一股浓烈的血腥味飘出来。那人好奇推开门,当场吓得屁滚尿流,连滚带爬地喊来了人。
根生叔死了,死在堆满稻谷的粮仓里。但那死状,绝非人力所能为。他全身赤裸,
被无数道细细的、坚韧的渔线密密麻麻地缠绕着,从脖子到脚踝,勒得紧紧的。
渔线深陷进皮肉里,把他整个人勒成了一块块凸起的、肿胀的肉块,
像一颗熟过头了、即将爆裂的石榴。鲜血浸透了身下的稻谷,染红了一大片。
他的眼睛布满血丝,瞪得几乎要裂开,脸上凝固着极致的痛苦和惊恐,
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拳头,仿佛死前看到了世间最可怕的景象。警察来了,勘查了半天,
最后也只能定性为“意外”,说可能是根生叔夜里去粮仓检查,不小心被散落的渔线缠住,
越挣扎勒得越紧,最终窒息而死。这个结论,连三岁孩子都不信。
什么样的渔线能自己把一个大活人缠成那样?又是什么样的意外,
能让一个人流露出那种表情?村里人心惶惶,流言像野草一样疯长。所有人都偷偷议论,
这是英子的鬼魂回来报仇了。听说,英子死的时候,
手里好像就攥着一截不知从哪来的破渔网线。根生家笼罩在巨大的恐惧中。
根生爷吓得病倒了,整日躺在炕上胡言乱语。英子娘则彻底疯了,她抱着一个破布娃娃,
满村子跑,见到年轻男人就扑上去撕打,喊着:“还我英子!你这个畜生!
”我爹娘也吓坏了。他们虽然恨根生家污蔑福来,但根生叔这死法太邪门了。
我娘连夜去镇上买了黄纸朱砂,在院子里烧了又拜,嘴里念念有词。
我爹则把家里的刀具都收了起来,晚上睡觉前要把门窗检查好几遍。
福来似乎也感受到了这股不寻常的气氛,变得更加焦躁不安。他有时会指着根生家的方向,
惊恐地尖叫:“红了!全都红了!疼!”我们只当他又犯了傻病,呵斥他闭嘴。
恐惧像瘟疫一样在村里蔓延。而我隐约感觉,这恐怕……才刚刚开始。4根生叔的死,
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地狱的门缝。村里关于英子冤魂索命的传言,已经不再是窃窃私语,
几乎成了公开的定论。人人自危,天一擦黑,家家户户就紧闭门户,路上绝了人迹。
根生爷的病,不见起色,反而越来越重。他不是躺在炕上呻吟,就是瞪着浑浊的老眼,
死死盯着屋顶,
嘴里反复念叨:“报应啊……报应来了……躲不掉……一个都躲不掉……”他那个大孙子,
英子的哥哥根旺,是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以前仗着家里男丁多,在村里横着走,
如今也吓破了胆,整天窝在家里,脸色蜡黄,眼珠子乱转,疑神疑鬼。我爹娘彻底坐不住了。
根生叔的死状像噩梦一样缠着他们。他们既怕根生家的诅咒下一个落到自己头上,
更怕英子的鬼魂认定是福来害了她,来找福来索命。我娘求神拜佛的频率更高了,
家里的香火味儿就没断过。我爹则变得异常暴躁,一点小事就摔东西骂人,
看福来的眼神也复杂起来,有时是心疼,有时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怨怼。没多久,
他们从邻村请来了一个姓王的道士。据说这王道士有些本事,能通阴阳,驱邪避凶。
王道士来的那天,是个阴天。他五十多岁年纪,干瘦,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旧道袍,眼神浑浊,
嘴唇耷拉着,怎么看都不像有道行的高人,倒像个落魄的江湖骗子。
他在我家院子里转了一圈,又去根生家附近瞅了瞅,眉头拧成了疙瘩。
“怨气重啊……”他捻着几根稀疏的胡子,摇头晃脑,“枉死的小鬼,怨气最是难除。
何况……这怨气里头,还夹着别的味儿。”我爹娘赶紧塞过去一个厚厚的红包,
求他无论如何要想想办法。王道士掂了掂红包,沉吟半晌,才说:“办法嘛,倒有一个。
开坛做法,请那孩崽子……哦不,请那位苦主上来,问问她到底有啥未了的心愿,
看看能不能化解。”做法事的地点,就设在我家院子中央,面朝根生家的方向。
时辰选在夜里子时,阴气最盛的时候。那晚没有月亮,只有几颗星子鬼鬼祟祟地眨着眼。
院子里点了香烛,摆上了供品,昏黄的光晕在夜风中摇曳,照得人影幢幢,更添几分阴森。
王道士披上件稍新点的道袍,手持桃木剑,嘴里念念有词,开始步罡踏斗。
我爹娘跪在法坛前,浑身抖得像筛糠。我躲在屋门后面,透过门缝紧张地看着。起初,
一切正常。王道士的咒语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可渐渐地,
我感觉周围的温度降了下来,一种渗入骨髓的阴冷弥漫开来。
法坛上的烛火开始不正常地跳动,颜色变得幽绿。王道士的动作突然僵住了。
他手里的桃木剑“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他整个人开始剧烈地颤抖,像是发了癫痫。
他的头不自然地歪向一边,眼睛向上翻,露出大片的眼白。喉咙里发出“咯咯”的怪响,
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脖子。我爹娘吓傻了,呆跪在地上,动弹不得。突然,
王道士猛地挺直了身子!他的脸,在幽绿的烛光下,完全变了模样。
不再是那个干瘦猥琐的道士,而是一种……一种难以形容的扭曲。
五官像是融化了又重新捏合,眼神变得空洞又怨毒,嘴角咧开一个极其诡异的弧度。
一个尖细、冰冷、完全不属于他的声音,从他喉咙里挤了出来,断断续续,
爹……爷……你们……是畜牲……”“娘……娘我死得冤啊……”“下一个……轮到……谁?
”这声音,我竟觉得有几分耳熟!是英子!是英子的声音!虽然变得尖利扭曲,但那调子,